 中国哲学史 第六章 湖湘性学
中国哲学史 第六章 湖湘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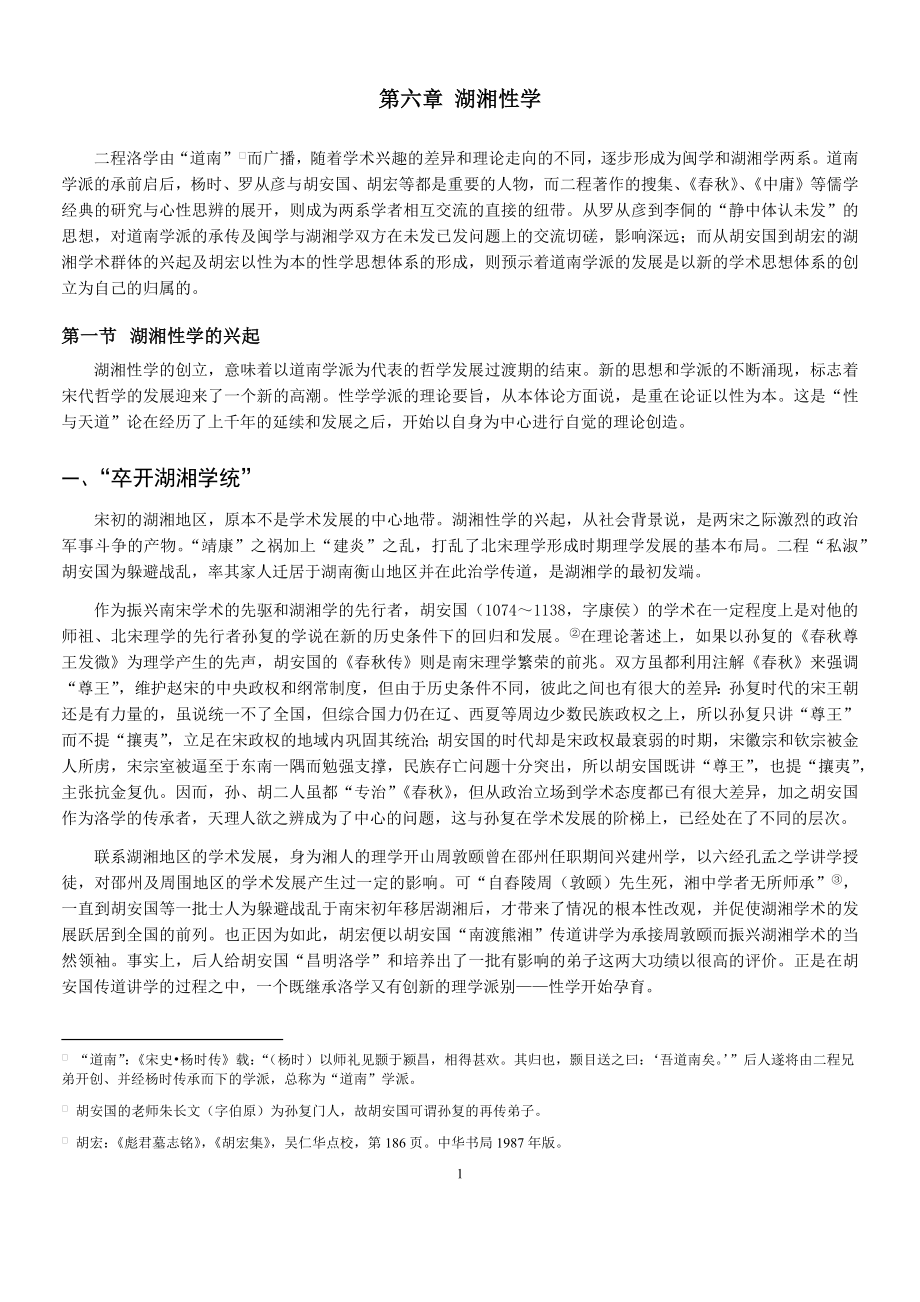


《中国哲学史 第六章 湖湘性学》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中国哲学史 第六章 湖湘性学(12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第六章 湖湘性学二程洛学由“道南” “道南”:宋史杨时传载:“(杨时)以师礼见颢于颍昌,相得甚欢。其归也,颢目送之曰:吾道南矣。”后人遂将由二程兄弟开创、并经杨时传承而下的学派,总称为“道南”学派。而广播,随着学术兴趣的差异和理论走向的不同,逐步形成为闽学和湖湘学两系。道南学派的承前启后,杨时、罗从彦与胡安国、胡宏等都是重要的人物,而二程著作的搜集、春秋、中庸等儒学经典的研究与心性思辨的展开,则成为两系学者相互交流的直接的纽带。从罗从彦到李侗的“静中体认未发”的思想,对道南学派的承传及闽学与湖湘学双方在未发已发问题上的交流切磋,影响深远;而从胡安国到胡宏的湖湘学术群体的兴起及胡宏以性为本的性学
2、思想体系的形成,则预示着道南学派的发展是以新的学术思想体系的创立为自己的归属的。第一节 湖湘性学的兴起湖湘性学的创立,意味着以道南学派为代表的哲学发展过渡期的结束。新的思想和学派的不断涌现,标志着宋代哲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性学学派的理论要旨,从本体论方面说,是重在论证以性为本。这是“性与天道”论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延续和发展之后,开始以自身为中心进行自觉的理论创造。一、“卒开湖湘学统”宋初的湖湘地区,原本不是学术发展的中心地带。湖湘性学的兴起,从社会背景说,是两宋之际激烈的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靖康”之祸加上“建炎”之乱,打乱了北宋理学形成时期理学发展的基本布局。二程“私淑”胡安国为躲避战
3、乱,率其家人迁居于湖南衡山地区并在此治学传道,是湖湘学的最初发端。作为振兴南宋学术的先驱和湖湘学的先行者,胡安国(10741138,字康侯)的学术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他的师祖、北宋理学的先行者孙复的学说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回归和发展。 胡安国的老师朱长文(字伯原)为孙复门人,故胡安国可谓孙复的再传弟子。在理论著述上,如果以孙复的春秋尊王发微为理学产生的先声,胡安国的春秋传则是南宋理学繁荣的前兆。双方虽都利用注解春秋来强调“尊王”,维护赵宋的中央政权和纲常制度,但由于历史条件不同,彼此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异:孙复时代的宋王朝还是有力量的,虽说统一不了全国,但综合国力仍在辽、西夏等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上,所以
4、孙复只讲“尊王”而不提“攘夷”,立足在宋政权的地域内巩固其统治;胡安国的时代却是宋政权最衰弱的时期,宋徽宗和钦宗被金人所虏,宋宗室被逼至于东南一隅而勉强支撑,民族存亡问题十分突出,所以胡安国既讲“尊王”,也提“攘夷”,主张抗金复仇。因而,孙、胡二人虽都“专治”春秋,但从政治立场到学术态度都已有很大差异,加之胡安国作为洛学的传承者,天理人欲之辨成为了中心的问题,这与孙复在学术发展的阶梯上,已经处在了不同的层次。联系湖湘地区的学术发展,身为湘人的理学开山周敦颐曾在邵州任职期间兴建州学,以六经孔孟之学讲学授徒,对邵州及周围地区的学术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可“自舂陵周(敦颐)先生死,湘中学者无所师承”
5、 胡宏:彪君墓志铭,胡宏集,吴仁华点校,第186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一直到胡安国等一批士人为躲避战乱于南宋初年移居湖湘后,才带来了情况的根本性改观,并促使湖湘学术的发展跃居到全国的前列。也正因为如此,胡宏便以胡安国“南渡熊湘”传道讲学为承接周敦颐而振兴湖湘学术的当然领袖。事实上,后人给胡安国“昌明洛学”和培养出了一批有影响的弟子这两大功绩以很高的评价。正是在胡安国传道讲学的过程之中,一个既继承洛学又有创新的理学派别性学开始孕育。湖湘性学的形成,经历了较长的时间,而胡安国、胡宏父子定居于衡山之下,创建碧泉书院、文定书堂授徒讲学,则可看作是它的开端。胡安国故去后,胡宏(11051162,字
6、仁仲,号五峰)在隐居衡山的20多年里,“玩心神明,不舍昼夜”,在总结“性与天道”论的理论发展史的基础上,以性范畴为中心构建出新的理论体系;又招徒授学,培养了大批弟子,张栻、彪居正、吴翌等便为其高足,“卒开湖湘之学统”,湖湘性学正式创立。胡宏于绍兴末年在衡山辞世后,由于张栻、彪居正、吴翌等弟子均在潭州(长沙)活动,湖湘学的中心也随之转移。张栻(11331180,字敬夫)其时虽年少,但由于父亲张浚的影响和他本人的学术造诣,已逐渐赢得了一批追随者。乾道二年(1166),湖南安抚使知潭州刘珙在岳麓山下主持修复了岳麓书院,延请张栻主教。张栻写下了著名的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讲明书院的目的是“盖欲成就人才,
7、以传道而济斯民也”,故“以为会友讲习,莫此地宜也”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全集,第695页。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湖湘学派以此为基地,迅速兴盛起来。乾道三年(1167),远在福建崇安的朱熹,鉴于张栻得胡宏亲传并在长沙讲学,由弟子林用中、范念德陪同来访,希望知晓胡宏之学。张栻和朱熹就作为理学基本理论的太极、中和、未发已发、察识存养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三日夜不能合”。这次讨论对朱熹“识乾坤”、“知太极”有重要的影响。接着,张栻和朱熹于岳麓、城南两书院展开“会讲”,长达两个多月,听讲者多至千人,“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盛况空前。会讲后期,彪居正、胡实等胡宏弟子也参加了进来。这可以
8、说是理学史上第一次规模宏大的学术讨论会和学术会讲,对南宋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受此影响,东南各省以及西南的四川等地都有学生前来求学,湖湘地区遂成为当时学术的中心之一,性学一派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八年后(1175),吕祖谦赴福建访朱熹,二人在朱熹的“寒泉精舍”共同研讨北宋理学家的著作,并编辑理学入门书近思录。同年,朱熹与陆九渊兄弟辩论于江西鹅湖,正式拉开了理学道学派和心学派长期论争的序幕。在这期间及稍后,有张栻于湖南、朱熹于福建、吕祖谦于浙江、陆九渊于江西,再加上浙东事功学派等各派学者的努力,合力推动南宋学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并由此而形成为比北宋理学更为精深和宏大的理学发展的新的高峰。湖
9、湘学作为宋代的著名学派,成果甚丰,胡安国的春秋传,胡寅的崇正辩,胡宏的知言、皇王大纪,张栻的论语解、孟子说,以及各自的文集等,是为主要的代表。二、性为天命全体和为学大体性学体系的总体概貌,如果参照胡宏在给其外甥的题词中所称“一见天地之全、古人之大体,庶几学有成立” 胡宏:题大学,胡宏集,第194页。的要求,其基本的标志,就在于抓住天命“全体”和古人为学之“大体”。那么,这种“全体”和“大体”意识可以说是湖湘性学“学成有立”的最重要的标志。这一标志性成果的意义,在于最终使“理学”与作为其对立面的“世儒”和佛老之学区别开来。在后者,或者沉溺于章句、寥落斯文而不能提举出儒学的“大体”;或者背违纲常、
10、别谈精妙而割裂性命之“全体”,从而只能成为他所坚守的以“性命理”学为标志的“儒门大业”必须要超越的对象。更为重要的是,在理学学术已经兴起的情况下,只有阐明“全体”和“大体”观念,才能使以性为本的思想,不但成为性学一系的理论基石,而且是会通理、气、心各家而构成整体理学的中介和枢纽。他说:大哉性乎!万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类指一理而言之尔,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者也。万物皆性所有也。 胡宏:知言一气,胡宏集,第28页。此一段可以说是胡宏定义性范畴地位的经典语言,其“万物皆性所有”,与张载的“性者万物之一源”和二程的 “性外无物”无疑有前后的联系,然而性学终究又不能还原到气学或道学。就张载
11、一方看,“性者万物之一源”只是说明了性为万物所共具,其结构是按虚性内在于实气的模式建立起来的,并非以性为最高范畴和哲学本体,而且,张载的性气结构也没有从天地性命全体的意义上去进行整合。他的以气为本,虽说是太虚即气,但作为“本体”的太虚只能解释无形,而无法直接说明气学体系的“全体”。在二程一方,虽说是性外无物,但性范畴的重心还是在人性自身,理才是整个宇宙的普遍和一般,不同人物个体所禀之性,均源于同一的天理本体,“性即理”也。同时,二程虽强调“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但尚未自觉地以“大体”、“全体”的意识作为本体的规定性和必要条件。不止是洛学,包括后来的闽学,理本论派虽也有性大理小的谈论,但总体上看
12、还是讲性小理大,“未有见天命之全体”。胡宏性学虽然源出于程氏一脉,但他之“万理具于性”的“理即性”关系模式,在形式上正是对二程“性即理”构架的颠覆。同时,胡宏讲性命的“全体”,又是与抓“大体”的思维相互发明的。他强调:列圣诸经,千言万语,必有大体,必有要妙。君若不在于的,苟欲玩其辞而已,是谓口耳之学,曾何足云! 胡宏:知言大学,胡宏集,第34页。圣贤千言万语,关键在天命全体,而全体中又有大体,有要妙,这在胡宏即是超越习于辞章的狭隘口耳之学,抓住具有最大普遍必然性的性的范畴,从而确立起性作为哲学本体和最高范畴的地位。可以说,胡宏通过自己提出的全体、大体意识的贯彻,利用讲“大体”来突出性本体的独立
13、性,使他所创立的性学,比之既有的气学和道学,事实上成为一种新兴的“理即性”的义理间架;而利用讲“全体”,又突出了各派理论之统合,从而为联结张、程气、理本体,最终构成为总体“理学”准备了充分的条件。所以他不是仅仅创立性学,也在于通过性的基础和中介来贯穿北宋各家,而且,性本体确立所需要借助的心实现性的心性合一架构,又为后来与心学的沟通打下了必须的基础。胡宏云:“天命之谓性,流行发现于日用之间。患在学道者未见全体,窥见一斑半点而执认己意,以为至诚之道。如是,如是,欲发而中节,与天地相似,难矣哉!” 胡宏:知言复义,胡宏集,第39页。天命之性流行发现是客观过程,但学道者要能够窥见“全体”,发而中节并与
14、天地相似,却完全取决于心的自觉,取决于在心中实现天命性体。所以,性学的全体观不能离开心而得以发明。而在大体的一方,同样也是如此。“大体”在胡宏也多次称作为“本根”。他有诗称:“孝弟须是知本根,万般功行且休论。圣门事业无多子,守此心为第一门。” 胡宏:赠人,胡宏集,第72页。流行日用之间,圣门事业的万般功行,首要的工夫就在于从一心入手,以察识本根为先导。如此而论“守心”,折射出性学心性合一的易简工夫的掠影。第二节 善恶不足以言性胡宏性本论的理论建构,与对性物关系或形而上下问题的思考分不开。性物一体的性的普遍必然地位,是他始终坚守的一个基本点。但由于传统的定势,论性一方面使“不可得而闻”之性变成了
15、可言可闻,另一方面又容易与人性善恶的问题相牵连,故要真正确立起性范畴的形上本体地位,就必须恰当阐明性可否言说的问题并破除将性与善恶捆绑在一起的观念,由此形成湖湘性学最具特色的“善恶不足以言性”说。一、性物一体与性之“指言”自周易而来的上道下器说,在胡宏是“上下”一体的关系。他认为双方就好像风与动、水与流一样不可割裂 胡宏云:“道不能无物而自道,物不能无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犹风之有动,犹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间之?”见知言修身,胡宏集,第4页。如此的道物一体,在性物关系上就是性物一体。后者要说明的,是性范畴的普遍必然地位。他说:圣人明于大伦,理于万物,畅于四肢,达于天地,一以贯之。性外无物,物外无性
16、,是故成己成物,无可无不可焉。 胡宏:知言修身,胡宏集,第6页。“一贯”于大伦、万物、四肢、天地的,惟有作为天地万物本体的性。因而,性外之物的存在从根本上说就是不可能的。既然如此,己性即是物性,成己即是成物,也就不再有可与不可之分了。胡宏强调,性本体固然是形而上的存在,形而上之性与形而下之物之间的区分也是必要的,但这并不妨碍人们对性本体的认识。他称:形而在上者谓之性,形而在下者谓之物。性有大体,人尽之矣。一人之性,万物备之矣。论其体,则浑沦乎天地,博洽于万物,虽圣人,无得而名焉;论其生,则散而万殊,善恶吉凶百行俱载,不可掩遏。论至于是,则知物有定性,而性无定体矣。” 胡宏:释疑孟辨,胡宏集,第
17、319页。 对于形而上的性体,圣人亦不能给它以确定的称谓;然而,性体通过其所作用的万事万物、善恶百行的生成变化,又无处不是在显示着自身的存在。那么,性物关系的奥妙,就是凡物都有自己确定之性,而性却没有固定不变之体,而是相应表现为不同事物的具体规定性,如火热水寒、父慈子孝等等。胡宏从性一与性殊的关系角度说明,由于万物备性而性之表现不可掩遏,人是能够充分体验性之“大体”的。但是,毕竟由于性体“不可得而闻”和圣人不能“名性”,性体能否被认知和言说,始终是一个问题。胡宏去世后,他的主要著作知言由张栻作序刊出,对湖湘学者及东南地区的理学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可是知言“论性特详”,主张以性为本,与论语“未
18、尝明言性”及儒家的传统不甚相合,以致包括彪居正等大弟子在内的不少人都产生了是否“与圣贤异”的疑虑。对此,张栻回答说:夫子虽未尝指言性,而子贡盖尝识之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是岂真不可得而闻哉?盖夫子之文章,无非性与天道之流行也。 张栻:胡子知言序,见胡宏集(附录二),第338339页。张栻为胡宏知言“论性特详”和以性为本思想的辩护,可以说是从揭示“性与天道”论的意蕴出发,对性物一体观作了进一步的发明。在这里,子贡之“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被解释为是子贡识性后的言谈。本体层面的“性与天道”虽然不能够直接闻见,但学者可以从“文章”诸物中去优游涵咏,体会感通。
19、按照张栻的梳理,孔子之后对于性与天道问题的铺陈,实际上有两种方式,一是明确“指言”,如“天命之谓性”便是;另一则是“未尝指言”,因为孔子的言谈“文章”,固无非性命之奥,无非天命之流行发现也。一句话,论语的立言,本来就是为展现孔子的天道性命。到了孟子,由于辟杨墨等异端的需要,不得不“指示大本而极言之” 同上。,发挥其心性之学,天命之性的全体融合进了孟子论性的大体。当然,从纯理论的角度说,名言概念对于形而上的本体的表达,往往十分地勉强。老子当年便有“强名”之说。那么,胡宏的“论性特详”就不如程颢的“性不容说”在理论上更站得住脚。但是,张栻阐明了胡宏提出性学的理论背景,认为在当时只有直接揭示出性之大
20、本,才能符合理论发展的客观要求,才能回应佛教“明心见性”的诪张雄诞之辨,才能挽救“丧失本心,万事隳驰”的儒家“高明之士”的沉溺,建立起儒家自己的心性哲学。就是说,“知言”的目的,在于使人知其言而悟其道,言与道、物与性始终是不可分割的。胡宏的性物一体观也表现在他对于性气等关系的论述中。他提出了“非性无物,非气无形。性,其气之本乎” 胡宏:知言事物,胡宏集,第22页。的重要观点。在性、气、形、物构成的结构中,“非性无物”固然有强调性为气之本,注重本体的地位和作用的意义,但它同时也是胡宏性物一体观的另一种表述,即无性则无物也可以表述为无物亦无性,这是在二程就已经明确了的。气形物之间,气为形的基础,物
21、则泛指成形之气,三者相对于性体又可以通用。合起来,讲以性为本并不等于忽视属于形而下的阴阳气化的存在价值,而是要求对性气双方进行细致的分析,以便在一体之中去把握“上下”。所以,湖湘学反对将性体视作为独立于气物之外的绝对存在者。性物一体观从流行的角度说,则又是对邵雍的阴阳动静说和张载论“太和”之道的继承。所谓“太和涵动静之性”,故而阴阳互动且作用不息也 胡宏:盘古氏,皇王大纪卷一,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源阁四库全书本,第313册,第9页。在这里,张载关于性为气所固有、性与天道“一于气”的主张对胡宏有重要的影响,胡宏的性物一体亦在于说明本体之性是内在于气物之中而决定气化流行的。但是,胡宏的论气比之张载
22、气学又有明显的差别,因为张载的性即天道是统一于气本;而在胡宏,气只是载体而不是本体,性才是性气、性物关系中的最后根据,“性立天下之有” 胡宏:知言事物,胡宏集,第21页。也。简言之,张载和胡宏的性气观,一是气为之本、一是气为性之本作论证。二、“叹美之辞”与善恶不足以言性湖湘性学以性为本观的建构,采用了张载、二程以来走乐记和中庸相结合路线的办法,即以乐记的“人生而静,天之性也”和中庸的“天命之谓性”作为其立论的基本前提。按胡宏的总结,告子当年因不知“天性”而讲“生之谓性”,所以遭到孟子的批评。胡宏总体上维护孟子,但也承认孟子的观点确有“未能从容中道”之处,所以后来才有如荀子主张性恶、需要通过“化
23、性起伪”的工夫走向仁义;又有如扬雄主张性善恶混,需要通过修其气禀才能使人去恶就善。荀、扬二人主张的一致性,在于都认为仁义是可以由后天培养教化而来的。进入宋代,司马光作疑孟而主张扬雄的性善恶混,却不明白本性与善恶的究竟,将形而上的先天同一本性与形而下的后天善恶百行混为一谈,所以胡宏要作释疑孟而与之辨。胡宏不赞成司马光的性说,有针对性地为孟子实乃为他自己的性学进行辩护。所以,胡宏的理论目的不在论证孟子“性善”,而是要将性与善相对剥离,发明“善恶不足以言性”,论证湖湘学自己的以性为本。从思想渊源说,二程就已经开始以赞美性之美好来解释性善。即“善”在二程并非意味着实在的德性,而是一种虚指,“以性之善如
24、此,故谓之性善” 程颐:遗书卷二十五,二程集,第318页。,善是作为形容词来使用的。二程对“性善”的新解到了胡氏父子,便被进一步发挥为叹美之辞。知言疑义记载:或问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则孟轲氏、荀卿氏、扬雄氏之以善恶言性也,非欤?”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奥也,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或者问曰:“何谓也?”曰:“宏闻之先君子曰:孟子所以独出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请曰:何谓也?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叹美之辞也,不与恶对。”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33页。性作为“天地之所以立”的根据和哲学本体,从逻辑上就可以判定与善恶的道德评价不在同一个层次,而应当是
25、超善恶的,不然,也就做不得本体。胡安国虽然肯定孟子“独出诸儒之表”而“知性”,其实“知性”者不是孟子而是胡氏父子自身。性作为哲学本体,已是最高范畴,除了赞叹其美好而外,连圣人也“无得而名焉”。而且,以性善为“叹美之辞”的架构,还可以解决性体“难名”又不得不名的问题,即利用“善”的名号去补充“性不容说”之缺失。但是,湖湘学以性为“叹美之辞”的观点,后来遭到朱熹的严厉批评,而被斥之为是佛教的“性无善恶”。因为朱熹始终坚守的,是孟子性善的基本原则。在朱熹,“若善底非本然之性,却那处得这善来!”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零一,第2586页。 这可以说是朱熹反对“叹美之辞”说的最根本的理由。由于“性即理”的基
26、础,朱熹确立天理本体的意义,实在于为人生、人世提供最后的价值基础。如果性不是本然为善,既会动摇至善天理的存在地位,也使人心失去了最为可靠的道德根基。从而,不但性范畴对人生和社会的价值效用随之丧失,也从根本上瓦解了儒家道德教化的可能,所以朱熹始终坚持性善的立场。但是,朱熹的立论和批评是基于理本论的立场,与湖相学的原意颇有偏差。因为湖湘学讲善恶不足以言性,是善恶作为后天的道德评价不足以言说先天本性,并不能简单倒过来说性不可言善,因为不论是讲“叹美之辞”还是赞美性为“天地鬼神之奥”,本身都可以是对性之“善”的阐发 牟宗三先生以为:“(胡氏)善不足以言之,况恶乎哉?此在字面上亦可译为性不可以善恶言,而
27、此语字面上又可转为性无所谓善恶或无善恶。朱子即由此直以告子性无分于善恶之说视之矣。此若非故意周纳,亦是误解之甚!若诚如此,则性又有何值得叹美处?”见所著:心体与性体中册,第38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在胡宏,性与理、善的关系,是性为万理之总体,善则是现实之理的规定和后天的道德评价。换句话说,要强调性的至上性,就有必要通过叹美之辞的手段将性本体与善相对分割,从而构成性无善恶(性无法言善恶)说。结合现实的评价活动看,善恶评价当然可以言说,但却不应与性之本体混同在一起。例如,在胡宏,要将圣人与众人区别开来,关键在本性的发现有中节不中节、或正或邪的不同,由此而给予“正者为善,邪者为恶”的评价
28、;但是却不应将此引申到本体,故“世儒乃以善恶言性,邈乎辽哉”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34页。!“节”属于社会的价值标准,后天人性或中节而正、或不中节而邪,善恶的评价于是施加于其上。但若将此后天的善恶评价直接用来规定先天本性,则是既动摇了性本体的地位,也不了解人的语言能力和范畴系统都有无法跨越的限制。由此,自孟子以来儒家的性善之说,就可以在赞叹性本体的宏大深奥,以致无其它语言可以形容的立场上去理解。在此前提下,与善相应的哲学范畴层次就可以分为二:一是作为“叹美之辞”的善“不与恶对”,只是形容赞叹的虚词,它要表明的是超越善恶而为天地鬼神之奥的性体;二是作为后天的价值评价标准的善,则
29、是与恶相对之善,它要表明的是善恶百行的性相,其与本然之性即哲学本体已经处于不同的理论层次。那么,在同为道南学脉的湖湘学与闽学之间的区别,按朱熹的概括,便是湖湘学的叹美之善(性本体)与善恶相对之善(道德评价)的“二性”说,与闽学的自天理而下的基于“性即理”构架的“一性”说之间的对立。双方虽然都强调了性的本然或形上的规定,从而使双方具备了相互联系而共组为统一学派理学的可能;但分别以性和以理为本,又使双方不得不区分为不同的体系。第三节 性体心用与察识在先胡宏的性本论是在对心性关系的阐发中建立起来的,但心性关系在胡宏包括不同的层面,从客观性方面讲是性体心用,这从结构的角度,保证了性范畴的根本地位和决定
30、作用。但是,作为胡宏性学基本范畴的性心双方,不是只在客观性的意义上被阐发。心不但不是被动消极的范畴,而是积极主动并直接担负着性体实现的使命。一、性体心用与未发已发性体心用的观点是胡宏在讨论圣人与道的关系时提出来的。知言曰:天地,圣人之父母;圣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则有子矣,有子则有父母矣,此万物之所以著见、道之所以名也。非圣人能名道也,有是道则有是名也。圣人指名其体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动,动则心矣。圣人传心,教天下以仁也。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36页。以父子关系来比喻天地与圣人的关系,说明天地的根源是通过圣人的现实活动得以证明的。在胡宏,万物能够“著现”的原因,是因为
31、有天地、有道来生成;而道能够命名的原因,是因为有子女、有圣人来发明。但这并非意味圣人有什么特殊的权威去命名道,而是圣人作为子女和万物的生成本身,就是道的现实。简言之,就是子女为父母的现实,父母为子女的根源。按此关系剖析道的范畴,道体的一方为性,道用的一方为心,从而出现性体与心用的范畴。胡宏通过从不动到动来描述性体与心用的关系,礼记乐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应当是来源之一。在后者,性本静,受外物所感又不得不动;而性一旦动作,其所谓“性之欲”已经属于心的范畴。性与心之间,胡宏以为双方的统一构成道的整体,但一方面,性作为体乃是第一位的,无性体即无心用也;另一方面,正如圣人证实着
32、天地而名道一样,心之活动作用也有效地证实着、实现着性之本体,无心用亦无性体也。所以,圣人“传心”,便能“教天下以仁也”。理学家的传心传道说,在胡宏这里得以简洁地揭示。道既有体用,则只能于用中见体,于心中见性,所以只能说“传心”而无法说“传性”;而所谓“传心”,又非为佛教传承的空无心性,而是体现为圣人通过仁德的弘扬教化天下的现实活动和过程。性体心用的问题又与未发已发的讨论相关。在胡宏,它们表现为一个本体与作用、未发与已发、静与动等诸范畴构成的多层次、多侧面的心性关系综合体。但基本的观点,是“未发只可言性,已发乃可言心” 胡宏:与僧吉甫书三首,胡宏集,第115页。本静之性是未发,动而发之心为已发。
33、体用虽是相互发明,但概念的区分还是必要的。在文本的层面,讨论心性动与不动的问题除乐记外,还有中庸和易传。胡宏说:某愚谓方喜怒哀乐未发,冲漠无朕,同此大本,虽庸与圣,无以异也;而无思无为,寂然不动,乃是指“易”而言,“易”则发矣。故无思无为,寂然不动,圣人之所独,而非庸人所及也。惟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更不用拟议也。 胡宏:与僧吉甫书三首,胡宏集,第116页。中庸提出的未发已发概念,按胡宏的理解,是当未发时圣人凡庸同享天性“大本”,本性同一。但中庸讲普遍大本却未及个别特殊,所以需要易传的补充。易传之“易”,本来就是指已发活动。但已发之心的存在状态有圣人与庸人的区别,圣人由于至高
34、的修养境界,能够使心保持在“无思无为,寂然不动”的静态,无须拟议便能感通万物之变化。胡宏在这里,实际上是用易传的思想修改了乐记的“感物而动”说。所谓“夫圣人尽性,故感物而静,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众生不能尽性,故感物而动,然后朋从尔思,而不得其正矣” 胡宏:与僧吉甫书三首,胡宏集,第115页。就是说,圣人由于已经“尽性”,故能够“感物而静”,心沉静专一而感通天下。乐记讲“感物而动”其实只是就众生而言,众生受外物的引诱和蛊惑,心躁动不已,而不能保持中正不偏。但是,胡宏强调,圣人庸人心的状态虽然有别,但在都属于已发上却是一致的,而不能将此与喜怒哀乐未发的性本身混同起来。湖湘学的性未发心已发观,从
35、胡安国、胡宏到张栻,是始终坚守的,而与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一系形成对立。双方的分歧,集中在中庸的“未发之中”与易传的“寂然不动”是同一的范畴还是差别的存在。闽学所持是前者,立足点在心对未发(性)已发(情)的统一;湖湘学所持是后者,故以未发之中为性,寂然不动为心。在这里,胡宏肯定心性“义各不同”而要求区分心性,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割裂。事实上,分别是为了更好的统一。他在论及心性的不同义涵时说:“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与未发已发不同。体用一源,不于已发未发而分也。宜深思之。” 胡宏:与彪德美,胡宏集,第135页。按照胡宏的思考,一方面,“不动”与“感通”是心自身的阶段之分,未发已发是性与心之分,二者不
36、属于同一个层次,不应混同。另一方面,在性与心双方,讲未发已发在逻辑上有“先后”之别,但从体用的角度说,又不能把它们分割为二。心的不动和感通作为性自身的活动和作用过程,本来也就是性本体存在的现实证明。没有心之用,也就没有性之体,双方表现为由体达用的统一。二、心以成性与察识在先胡宏分辨心性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突出心的主体地位,使心范畴直接担负起性之完成和实现的使命。他说:“天命之谓性。”性,天下之大本也。尧、舜、禹、汤、文王、仲尼六君子先后相诏,必曰心而不曰性,何也?心也者,知天地,宰万物,以成性者也。六君子,尽心者也,故能立天下之大本,人至于今赖焉。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28页
37、。性作为天命,固然是宇宙的本体,但儒家的道统前后相传,圣人间所叮嘱的都是“心”而不是“性”,道理何在呢?一方面,性作为天下之大本,它是通过心之活动作用去实现和证实的,所以言心用自然就说明了性体。另一方面,性的普遍本体在个体人物的成就,离不开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成性”在这里是特指性本体在人心中的自觉挺立,而这便需要充分扩充人的本心去实现,即尽心以成性也。圣人为万民之先而确立起来的“天下大本”,是人伦日常得以不衰、异端不得并作而学术归于一统的最根本的保障。以圣人为典范的“心以成性”说,中间有一个状语来修饰,或者说为心实现性规定了条件,这即他提出的心必须“知天地宰万物”才能成其性。意味心作为主体,
38、固然需要心的内在体验扩充以挺立性体,但这又不能离开心面向天地万物的交流感通和主宰的作用。张载的大心而体天下之物可以作为理解的参考,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也。同时,心知天地、宰万物与二程以来的“即物穷理”、“穷理尽性”的工夫也可以相互协调。在胡宏,尽性、成性与穷理等表述不一,但实质上却是相似的。所以他又有“心穷其理,则可与言性矣”;“穷理尽性以成吾仁” 胡宏:知言纷华,胡宏集第25、26页。等多种说法。成性其实就是成就仁德,仁体或性体之“成”就在理之“穷”的过程中,而不是在此之后或之外。一句话,心知天地宰万物就是尽心成性或穷理尽性。因而,“心以成性”或“尽心成性”的道路,虽说是在主体的道德创造中实
39、现本体,但这同样也是一个客观化的过程。胡宏要求“不行己之欲,不用己之智,而循天之理,所以求尽其心也” 胡宏:知言天命,胡宏集,第4页。尽心不能脱离开客观天理的参照。这也表明胡宏的性本体与洛学的理本体之间的前后承接的关系。性体的客观性是胡宏始终坚守的。如他又说:“性定,则心宰,心宰,则物随”“性定”是“心宰”的客观基础和必须前提,心不能不循于性本身的内容和规定,并且以性体的实现为惟一的使命和目的。“心宰则物随”与心“知天地宰万物”是同一的含义,心如能穷理尽性,我心与外物、我性与物性完全融通为一,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也。在这里,集中体现这一最终境界的范畴是“诚”,“诚成天下之性” 胡宏:知言事物,胡宏
40、集,第22页。也。由“诚”来标示性本体的实现,意味着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内在性而与外在的客观性融合为一。如此超越融合的境界或“心以成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对察识与存养关系的恰当处理。胡宏在认识和践履活动中,始终坚持有的放矢的原则。以为若不是这样,则从根本上迷失了为学之大本,结果不但谈不上上升到与天地一体的境界,而且还会被释氏所牵引,以致完全偏离大学的正道。道理很简单,“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处己,乌能处物” 胡宏:知言一气,胡宏集,第28页。?对自己都没有恰当定位,又怎么能正确把握天地万物呢?所以,从一般的知行关系说,“天下万事,莫先乎知矣。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 胡宏:知言汉文,胡宏集
41、,第43页。心实现性而挺立天道,首先要知道什么是天道。同样,儒者进学,也就要先穷理,理明然后物格知至、意诚心正。从一般的知行关系进入到仁德的认识和践履,集中体现在胡宏的“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34页。的观点中。他虽未明言何为“仁之体”,但从其论述可以看出是指仁德的存在和发端,故“为仁”的重点不在一般地发明“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而在于从“以放心求心”的实践中去发现苗裔并涵养扩充,从而在实践中解决万物与我为一的问题。他设问说:“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自己回答道:齐王见牛而不忍杀,此良心之苗裔,因利欲之间而见者也。一有见焉,操而存
42、之,存而养之,养而充之,以至于大,大而不已,与天同矣。此心在人,其发见之端不同,要在识之而已。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35页。在胡宏,良心苗裔总是会在利欲的空隙中表现出来,一当发现便应及时体验操存,涵养扩充,最终达致与天地合一的境界。当然,“发见之端”因时因人而有别,关键在恰当地识别把握。这可以说是胡宏致知在先原则在修养说中的运用。因为不能无目的地“操存”,必须要先知“的”,然后方可“积习而求中的”。胡宏的这一观点,后来发展为湖湘学察识先于涵养的一般原则,而与闽学一派涵养先于察识的主张形成对立。张栻在他的名篇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中,按照察良心苗裔而操存扩充的模式阐发说,人们“终日
43、事亲从兄、应物处事”,而仁之端“其或发见,亦知其所以然乎?诚能默识而存之,扩充而达之,生生之妙油然于中,则仁之大体岂不可得乎?”而“及其至”,则是“与天地合德,鬼神同用,悠久无疆”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全集,第694页。,实现了胡宏所要求的结果的“与天同矣”。张栻将胡宏的前后思想集中作了概括,使之更加规范化了,即识仁之体是一个识端、存养而得体的辩证统一过程,最终的目标是天人合一。这说明了张栻在继承胡宏思想的过程中又有所发展,并与朱熹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长期的争辩。第四节 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北宋理学对天理人欲问题的基本看法,是理学家们均要求克制个人的欲望以顺从和复归于天理。张载、
44、二程在本体论上虽然有别,在道德观上却是大同小异,他们都注重天理人欲之辨,这一基本的价值导向,影响了后来整个的理学发展。但在理学思潮中也存在另一种思想倾向,即要求承认欲望的合理性,主张将理欲与统一起来,这首先便是湖湘学提出的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说。一、理欲同体同行与区分的标准理学家对天理人欲之辨的强调并未妨碍世人对人欲的追求,事实上,人欲反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支配着人心,从而危及到儒家学术的传承。如胡宏所说:生本无可好,人之所以好生者,以欲也;死本无可恶,人之所以恶死者,亦以欲也。生,求称其欲;死,惧失其欲。冲冲天地之间,莫不以欲为事,而心学不传矣。 胡宏:知言文王,胡宏集,第18页。正统的儒
45、学或理学被胡宏称作“心学”,突出了“传道”重在“传心”的鲜明理学特色。但显然“心学”不敌人欲,以致于“冲冲天地之间莫不以欲为事”。这表明欲望的存在有它的客观性和必然性,并实际左右着人们从生到死的一切活动。由此,“心学”就必须要考虑如何在容忍欲望存在的前提下去弘杨天理和引导人们对天理的追求。天理人欲“同体异用”、“同行异情”说就产生于这一思想背景之下。胡宏说: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同行而异情。进修君子,亦深别焉。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29页。“同体异用”与“同行异情”前后意思相关,“同体”、“同行”是说理欲双方共存于同一事体及其活动流行之中,“异用”、“异情”则表明天理人欲虽同体
46、共存,却有着不同的作用和表现:天理满足的是道义的要求,人欲却服务于生存的需要。所以,君子的修身养性,需要在同体、同行中去认真地分辨异用和异情。胡宏的这一思想使他成为理学阵营中最早肯定人欲的合理地位之人。因为他表明了从“同体”、“同行”中去辨别“异用”、“异情”,实际上只能从价值评价上来进行,在客观事实上是分辨不清的。也正因为如此,这种分辨才十分地不易。那么,立足于哪里、从何处出发来评价就是胡宏更为关心的问题。因为私利与道义同为人所需要,关键在以谁为主导,主体的判断和选择在这里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比方说:“夫妇之道,人丑之者,以淫欲为事也;圣人安之者,以保合为义也。接而知有礼焉,交而知有道焉,惟
47、敬者为能守而勿失也。语曰:乐而不淫,则得性命之正矣。谓之淫欲者,非陋庸人而何?” 胡宏:知言阴阳,胡宏集,第7页。在客观事实上不变的夫妇之道,从价值观念上却可以作出不同的评价,因为借以评价的标准及动机不同。鉴于道不离物的一般前提,人与外物相交接的任何活动都有礼、道存于其中,但要为人所自觉把握,只有居敬持身之人才有可能。他引来孔子的“乐而不淫”作为根据,肯定“性命之正”就存在于和乐而不过分的欲望的抒发之中。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所谓丑事、淫欲,只是那些将性命天理与人世欲望割裂开来的庸人们的愚腐见解。因而,在日常的事物活动之中,立足于哪里、从何处出发来进行评价就是十分重要的。这里的所谓事物活动,既包
48、括对象性的,也包括人自身的,譬如好恶便是出于人自身的情感活动。好恶人人皆有,区分君子还是小人,不在于好恶本身,而在于立足于什么去好恶。如云:“好恶,性也。小人好恶以己,君子好恶以道。察乎此,则天理人欲可知。”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30页。爱好或憎恶的情感出于人的本能,在这一点上,不但区分不开君子和小人,事实上,连人和动物也是区分不开的。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它的道德基础,即立于私利还是立足于道义。二者虽同为人所需,分别满足于人的肉体和精神的不同需求,但却存在以谁为主导的问题,主体的判断和选择在这里起着最后的决定作用。代入好恶的情感活动,则基于私利而好恶为小人、为人欲,择于道义而
49、好恶则为君子、为天理。察乎此,天理人欲虽然同体、同行,但终于能得以区分。圣人、君子的高人一畴,也正是从这里表现了出来,他们并能自觉以所选择的天理为立身行事的根据。二、“公欲”与中节尽管二程的人欲并不等于私欲,双方有一般与个别之差,但后来人欲与私欲实际上变成了同一的概念,如此的混淆对肯定人欲的合理性是十分不利的。胡宏“公欲”概念的提出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实际上,在胡宏理欲“同体异用”的模式中,高擎一个天理而与日常生活欲求相对立的氛围已经被消解,而转换为在肯定人欲存在的必要性的前提下推尊天理的新的努力。道理很简单,“同体”造成了在否定欲望的同时就必定会否定天理,所以否定欲望既不现实,又不可能,唯
50、一可行的,只能是采取引导的办法使之向善。他说:夫人目于五色,耳于五声,口于五味,其性固然,非外来也。圣人因其性而导之,由于至善,故民之化也易。老子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夫可欲者,天下之公欲也,而可蔽之使不见乎? 胡宏:知言阴阳,胡宏集,第910页。感官欲求出于人的天性,人人有感官欲求,人人也都希望满足天性的需要,即所谓“公欲”也,根本无法也不可能蔽之使不见。圣人的教化民众,只能是承认欲望而纯化其动机,采取引导的办法使民向善。老子想要通过“不见可欲”的封闭的办法来戒除人们的欲望和保持人心的纯真,根本是行不通的。当然,“寡欲”的理念自孟子提出之后,所有儒家的后继者都是认同和坚守,所以胡宏也主
51、张“修身以寡欲为要” 胡宏:知言修身,胡宏集,第4页。但“寡欲”并不等于无欲、禁欲,这一界限是应当划分清楚的。所谓寡欲,就是在肯定欲望合理性的前提下,对欲望进行适当调节,屏弃和戒除过分的贪求,使其不超过一定的限度,即所谓“中节”。这样的欲望就既是客观的又是合理的,圣人便是实现了这二者的统一。如称:凡天命所有而众人有之者,圣人皆有之。人以情为有累也,圣人不去情;人以才为有害也,圣人不病才;人以欲为不善也,圣人不绝欲;人以术为伤德也,圣人不弃术;人以忧为非达也,圣人不忘忧;人以怨为非宏也,圣人不释怨。然则何以别于众人乎?圣人发而中节,而众人不中节也。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3333
52、4页。圣人作为完美的理想人格,为所有理学家所共同尊奉,但胡宏的圣人显然有自身的特点,即他的“完美”性是相当彻底的,众人所有的特性圣人无一欠缺。圣人之为圣人,决非他摒弃了一切情欲,而是他能恰当地处理这些情欲,使它们都能恰到好处,无过无不及。如果有一样情欲圣人不具,圣人就不是完美的人格了。而且,人的情欲从其本能的发动来说,也是由天所命而不得不然的,虽然可以“寡”,但却不能“绝”,绝了则等于否定了天命本身,所以是万万不可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利用了圣人和天命概念的不可侵犯性来为他的欲望的合理性作论证的,既考虑了道德信仰的要求,也保证了人的切身利益之所在。那么,胡宏对于欲望的观点就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
53、从事实方面所给予的肯定的回答,无此必不行;而在价值评价一方,由于众人欲望的不能中节,也就不能给予善的评价:“中节者为是,不中节者为非;挟是而行则为正,挟非而行则为邪;正者为善、邪者为恶。” 见胡子知言疑义,胡宏集(附录一),第334页。从而,圣人的教化和引导就是必要的,以期达到一种主观上不以欲为念,对外在的利害得失不予计较的平常心态。他说:“人欲盛,则天理昏;理素明,则无欲矣。处富贵乎?与天地同其通。处贫贱乎?与天地共其否。安死顺生,与天地同其变,又何宫室、妻妾、衣服、饮食、存亡、得丧而以介意乎?” 胡宏:知言纷华,胡宏集,第24页。从渊源上讲,这里可以追溯到周敦颐的“道充为贵”说和张载的“民
54、胞物与”说,但胡宏却突出了“不介意”的心态。如果能与天地同其变通,自然就超越了计较个体的利害得失,这与他物我一体的本体论和修养说是相衔接的。整个世界既然是一个大我,何物非我,何我非物,就不应去计较小我的贵贱生死、存亡得失。同时,更重要的是,外在的物质条件、物质享受对人的精神追求和境界提升来说,虽说是必不可少的手段,但这就如同渡河之舟、跨涧之梁一样,它们对于实现渡河或人格修养的目的,只能起辅助的和暂时的作用。所谓“江河之流,非舟不济,人取其济则已矣,不复留情于舟也。涧壑之险,非梁不渡,人取其渡则已矣,不复留情于梁也。人于奉身济生之物皆如是也,不亦善乎!澹然天地之间,虽死生之变,不能动其心矣。” 胡宏:知言文王,胡宏集,第18页。人若能达到不为外物所动而静心于对天理的追求,便是人的价值的最高体现。胡宏的“不介意”可以说是在主观层面实现“中节”的必须前提,主观上做到不介意,客观上便自然能中节,圣人已经为世人提供了最好的标准。胡宏肯定欲望的合理性,又倡导精神价值的优先性,如此的理欲统一观与成为理学主流的存理灭欲观相对立,为存理于欲思想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先导作用。12
- 温馨提示:
1: 本站所有资源如无特殊说明,都需要本地电脑安装OFFICE2007和PDF阅读器。图纸软件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压缩文件请下载最新的WinRAR软件解压。
2: 本站的文档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图纸等,如果需要附件,请联系上传者。文件的所有权益归上传用户所有。
3.本站RAR压缩包中若带图纸,网页内容里面会有图纸预览,若没有图纸预览就没有图纸。
4. 未经权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将文件中的内容挪作商业或盈利用途。
5. 装配图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保护处理,对用户上传分享的文档内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编辑,并不能对任何下载内容负责。
6. 下载文件中如有侵权或不适当内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立即纠正。
7. 本站不保证下载资源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时也不承担用户因使用这些下载资源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