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立的有效性前提
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立的有效性前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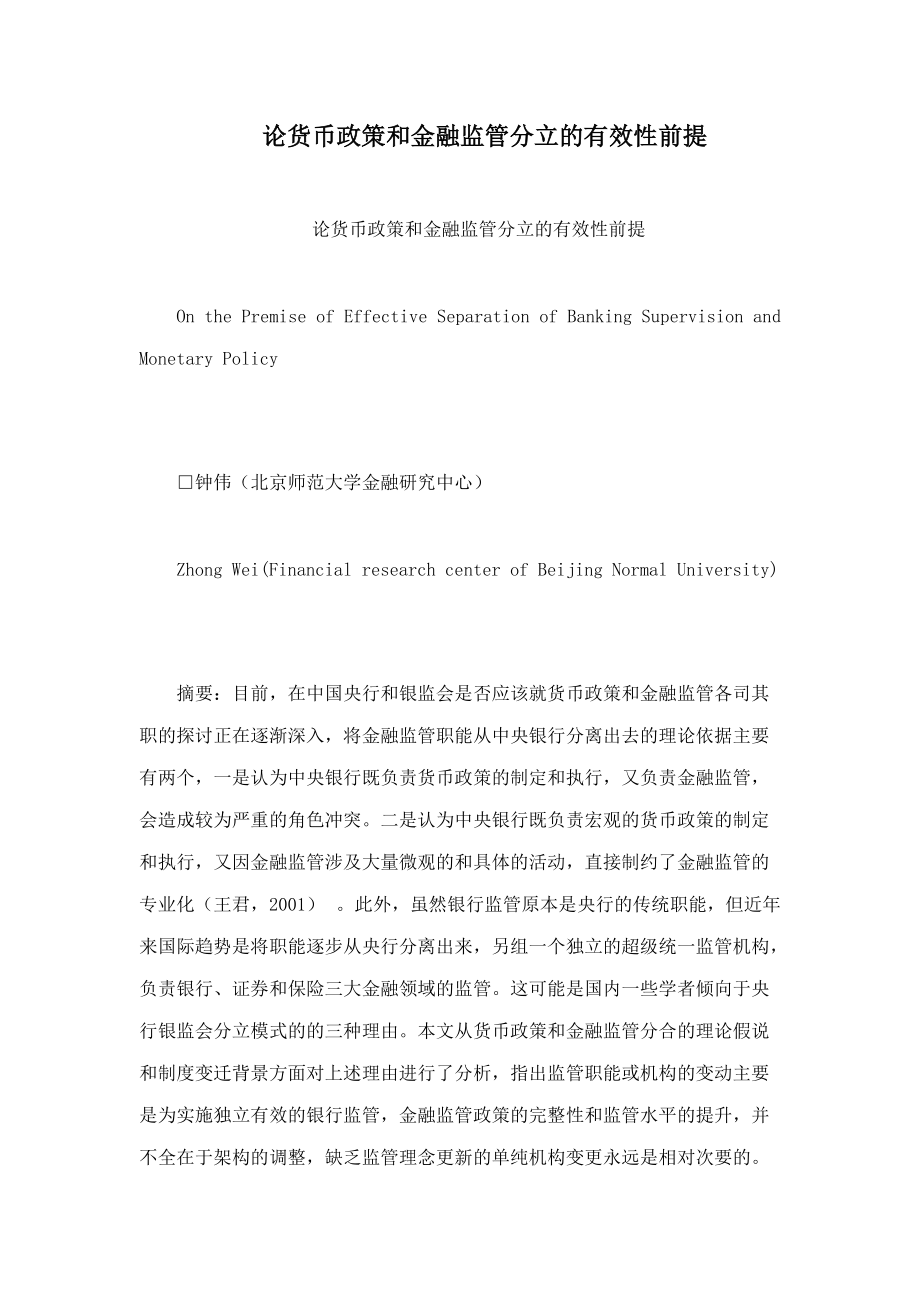


《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立的有效性前提》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立的有效性前提(19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立的有效性前提论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立的有效性前提On the Premise of Effective Separation of Banking Supervision and Monetary Policy钟伟(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Zhong Wei(Financial research cente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摘要:目前,在中国央行和银监会是否应该就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各司其职的探讨正在逐渐深入,将金融监管职能从中央银行分离出去的理论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认为中央银行既负责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又负责金融监管,会造
2、成较为严重的角色冲突。二是认为中央银行既负责宏观的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又因金融监管涉及大量微观的和具体的活动,直接制约了金融监管的专业化(王君,2001) 。此外,虽然银行监管原本是央行的传统职能,但近年来国际趋势是将职能逐步从央行分离出来,另组一个独立的超级统一监管机构,负责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金融领域的监管。这可能是国内一些学者倾向于央行银监会分立模式的的三种理由。本文从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合的理论假说和制度变迁背景方面对上述理由进行了分析,指出监管职能或机构的变动主要是为实施独立有效的银行监管,金融监管政策的完整性和监管水平的提升,并不全在于架构的调整,缺乏监管理念更新的单纯机构变更永
3、远是相对次要的。关键词:统一金融监管;货币政策 角色冲突 最后贷款人 Abstract:The paper discusses three reasons that supports the separation of banking supervision function from the central bank, firstly, the combination of supervision and monetary policy may result in conflict of interest, secondly, the such combination hampers the
4、 specialization of banking regulatory system, tertiary, there is a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financial supervision1>. We points out that the effective separation of banking supervision function from central bank in China has several premise among which the independence of central bank is at most im
5、portance. Key Words:Integrated Financial Supervision; Monetary Policy; Conflict of interest; The Lender of Last Resort 一、中央银行的“双重角色冲突”及其外部化关于央行在执行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时的“双重角色冲突”是人们倾向于央行和监管部门机构分立的主要理由。对角色冲突的通常说法是,央行身兼二任时,会更倾向于少采取不利于银行体系利益的事情(例如降低利差),结果央行在制定和实施监管时成为商业银行的“监管捕获者”(Regulatory capture),因为央行过多地考虑了保护银行而
6、非公众的利益。但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应该合并还是分立从来都是广受争议的难题,而分合选择通常取决于一系列因素,包括一国金融体系的特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独立性是否已得到保障,以及中央银行的现状在多大程度上同时影响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有效性等(Joseph.Haubrich,1996) 。就中国的情况而言,角色冲突的确存在,例如央行若决定调整利率,那将明显地影响银行体系的盈利能力,甚至可能由于货币政策失误而触发银行危机。央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可能对金融监管持较为松懈的态度,例如对银行资本金的不足、对不良资产的积累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如此央行兼具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双重职能时,必然会诱发其内在的通货膨胀
7、倾向。另外还有两个理由可以支持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政策的分离,其一是货币政策总是灵活的,而金融监管政策必须是一以贯之的,监管不可能也不应该随着货币政策姿态的调整而偏离市场中立姿态;其二是货币政策总是逆周期的,即在经济高涨时紧缩而在衰退时扩张,以图熨平经济周期,而金融监管政策总是顺周期的,即在经济高涨时商业银行因效益较好而降低了监管难度,而在衰退时银行监管的难度也随商业银行绩效的滑坡而增加。但是总体上角色冲突也可以视为一个悖论,即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分离,并不意味着克服了角色冲突的难题,而仅仅是内部冲突的外部化而已。 如果央行身兼二任是有问题的,那么通过独立于央行的银监会的模式,将金融监管职能分离
8、出去,也会导致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时,偏离银行体系的承受能力。货币政策的目标当然是通货的稳定,但货币政策的调整也不能不考虑金融机构的财务状况,一旦金融监管从央行中剥离,那么货币政策决策时就可能缺乏足够的金融监管信息的微观支撑。在央行身兼二任时,央行不存在货币政策信息和金融监管信息之间的不对称性,它都充分地了解这两个层面的信息,在央行和银监会各司其职后,央行将享有充分的货币政策信息和不完备的金融监管信息;而银监会享有充分的银行监管信息和不完备的货币政策信息。当然有两种渠道可以部分弱化央行和银监会分离后带来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第一种渠道是中央银行通过支付清算体系,可以方便地监控银行的资金流向和流动性
9、,也可以通过非现场手段收集银行信息。但上述渠道获得的银行微观信息仍无法替代金融监管的第一手资料。第二种渠道是加强央行和银监会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例如在2000年,我国在人行、证监会和保监会之间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以加强三大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当然未来联席会议完全可以再增加银监会,但联席会议制度显然不足以完成上述诸多使命,信息共享的时效性和全面性都必然与央行身兼二任时同日而语。 更为严重的是,通过设立银监会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相互冲突的外部化,可能削弱央行较为准确地行使最后贷款人角色。在央行身兼二任时,若央行执行紧缩型的货币政策,则在金融监管时也可能更为苛刻,以达到紧缩的效果,但这种苛严有一个
10、底线,即央行显然试图将监管的苛严控制在不至于导致银行遭遇过分的流动性短缺而影响银行存续的地步,以免银行倒闭使得央行不得不背上履行最后贷款人的沉重负担。而在央行执行扩张型货币政策时,则在金融监管时也可能更为宽柔,使得央行因货币政策基调的改变而难以保持监管中立姿态,并从中长期来看央行会带有通货膨胀的冲动,影响了金融监管的连续性。但毕竟央行央行由于金融监管而非常了解银行体系的承受力,并在货币政策制定时更多地考虑此因素,以避免央行频繁地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责。从西方国家的情况看,金融监管之所以需要独立出去,就在于监管对象,即原先边界清晰的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机构的功能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使得央行的监管效
11、能下降。如果一国央行没有直接面对这样的挑战,那么央行-监管的机构分立反而可能对金融稳定不利,金融体系的系统性性风险可能趋于上升(Charles.Goodhart,2000) 。如果央行和银监会各司其职,那么也许可以部分克服央行金融监管顾虑最后贷款人义务,而导致的金融监管的非中立姿态,新的更严重的问题也孳生了。银监会作为单纯的银行监管机构没有创造货币的功能,因此也没有能力为陷入困境的银行体系提供流动性。而央行要妥当运用最后贷款人职能,却有必要充分了解具体银行的经营状况,如果央行没有监管职能,会发生其信息、责任、权力的不对称,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将更多地依赖银监会对银行困境的判断而不是自身的判
12、断,这将导致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及时效的明显下降,或运用过滥,从而引发道德风险;或运用过严、过迟,从而错过防范银行危机的最佳时机。简要的结论是,如果央行身兼二任,那么央行具有某种通货膨胀的倾向的同时,对行使其最后贷款人职能时,往往可能救助介入过早,以避免事情发生得不可收拾。而在央行和银监会各司其职,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能时,比救助过早更为糟糕,鉴于金融监管状况和救助请求更多地来自银监会,那么央行此时在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时,已经不是“建设性地模棱两可”(constructive ambiguity)的市场中立姿态这是为避免银行体系因救助条件的明确性而滋长道德风险的必要姿态(Xavier.Fre
13、ixas) ,而是因银监会的存在央行将感受到对救助动因和效果的某种责任转嫁因素,因此央行行使最后贷款人时审慎性可能明显削弱。二、金融监管的专业化和机构变革关于中央银行身兼二职将影响金融监管专业化,是构成金融监管机构应独立于央行的另一重要理由。随着金融全球化的深化、IT技术对金融业的深厚影响,以及金融混业浪潮的迅猛发展,金融监管的确面临着非常紧迫的专业化要求。而作为存款性金融机构的银行的监管专业化问题尤其突出,据说很多有问题银行在临倒闭前的五分钟,资产负债表还是好的。而一旦问题暴露则一发难收,迅速瓦解存款人的信心(王君,2002) 。如果缺乏高度专业化的金融监管,那么面对上述问题就可能既在事先缺
14、乏对有问题银行的系统有效的预警机制,又缺乏在监管过程中敏感地捕捉和发现问题的能力,更缺乏在事后对有问题银行的救助体系,结果非专业化的金融监管或对危机视而难见,或贻误处理问题的时机,或徒劳无疑地对明明挽救无望的银行进行代价昂贵的救助。 那么金融监管的专业化是否就是另设机构?恐不尽然。在如何通过改变机构设置提高金融监管方面,中国做了不了努力,其中较大机构变动有两次。第一次努力是在198><#004699'>98年的11月,那次机构变动是取消了央行省级分行,取而代之的是九大区分行和21个地方监管办。央行总行架构也进行了调整,基调是按境内外、表内外、本外币、现场非现场监控融为
15、一体的思路重新进行机构设置,设计初衷似乎是为了避免在金融监管过程中,地方政府对银行的过度干预问题,并且方案本身也考虑了国内外金融监管的一些经验。但从实际效果看来,不尽如人意,央行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未能根本改观。 现在总结这次监管机构变革未能带来监管效能改善的教训,集中起来可概括为:1、机构改革方案出台仓促,对金融监管政策的总体设计尚欠周全。19<#004699'>98年3月,人大确定了央行在全国设置9-12个大区行的基本思路,直到10月机构变动前夕才拿出具体的征求意见稿,而随后的短短两个月内,新设置的九大区分行就全部挂牌。目前如果央行和银监分离,则不能不考虑方案的充分酝酿和讨
16、论,以未雨绸缪,毕竟有效的金融监管不是一蹴而就的。2、机构设置虽变动,但明显缺乏对机构定位和监管权限的清晰界定。在央行-大区行-监管办设立之后,监管权限应是央行集中金融监管决策,下级监管部门在授权范围内具体执行,并将执行中的问题和建议及时反馈给总行。只有在地方情况特殊并经总行授权的情况下,才能制订地方性规章。但实际情况却是央行失职和下级机构越权兼而有之。机构变动除了增加监管层级和造成监管办对商业银行省分行的监管困难之外似乎实效不大。3、监管政策研究、制定和执行的专业化水准无明显改善,这和原有错综复杂令商业银行无所适从的原有监管措施没有重新厘订成相对清晰可行的监管框架、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行体制没有
17、相应改观、银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发育滞后、银行用人机制不到位、立法执法环境不成熟等诸多因素相关。另一次努力是在2001年的9月,这次金融监管的机构变动主要内容是:1、引入美国货币监理署“派驻监管组”的经验,在银行监管一司增设四个国有商业银行监管处,各大区分行增加相应的机构,原21个行监管办改属一司,负责对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的日常和现场监管;2、银行监管二司专司对股份制商业银行监管,而各省中心支行改属银行监管二司,主要监管当地的中小金融机构;3、依据“管监分离”的思路,在原监管一司及二司之外,成立新的银行管理司,负责所有与市场准入、退出、监管政策研究等属于“管制类”的业务。试图让银行管理司独
18、立负责宏观的银行监管政策的研究和制定,而银监一司和二司负责微观的日常和现场监管。管监分离的尝试仍不甚令人满意,除了惯有的仓促改革问题之外,缺乏整体性的监管政策框架,缺乏实施哪怕是和适度改进的“管监分离”相适应的监管资源重新配置,以及缺乏银监一、二司和管理司之间的有效协调等,都使得用意良好的央行金融监管内部机构变动不能奏效,除了增加了一些副司和处级干部配备之外,日常和现场监管人员没有明显扩充。在讨论金融监管的独立性时,不应该忽视这样的隐忧,即就中国银监会而言,它可能既是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又是整个银行业的监管者。因为就目前的政府机构变动来说,国资委虽然是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但金融企业的资产不在
19、其列,银监会充当着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却必须监管全部的国有和非国有商业银行,这就难以避免在监管中厚此薄彼的倾向。因此,银行监管机构变动本身并不足以带来金融监管专业性和有效性的提高,所谓金融监管的专业性,不仅需要银行监管官员具备专业素质,更重要的是,在另起炉灶设立金融监管机构之前,必须建立一套合理的而不是沿用原来千头万绪的金融管制措施的、以风险管理为主的监管框架,必须设立专门的宏观审慎和微观审慎监管政策的研究部门并充实足够的有实际监管经验的专业研究队伍,必须清楚如何自上而下地设立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如何在这些机构间进行集中和授权,必须清楚金融监管政策借助何种监管传导机制(例如银行业协会、具有相对完善的公
20、司内部治理结构的商业银行等)才能奏效,必须考虑货币政策与银行监管政策的信息共享,使央行和银监会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和协作,必须使非现场监控与现场检查能有序协调,既充分监管,又不破坏商业银行经营的规律,上述种种问题是在实施机构变革之前应予充分考虑的(陈工孟,林朝华,2001) 。否则央行和银监会的机构分立,就可能难以带来真正的金融监管专业化,而更可能是银行监管在低水平上的简单重复甚至倒退。在以专业化提高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时,尤其应该关注监管政策的传导机制问题,毕竟任何制度变迁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典型的例子是虽然中国近年来货币政策的基调大体适宜,但因货币传导机制的阻塞而使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受
21、到困扰。目前看来,独立有效的金融监管政策同样需要顺畅的传导机制,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考虑下列问题:1、监管政策的研究开发是否和原有的离散型监管政策的清理整顿同步进行?监管政策的制定包括审慎监管规章的制定,当然也包括对原有规章的修订、补充或废止。否则尽管机构另设了,但监管不足和监管过度并存的不正常现象却难消除。2、监管人员的专业化集聚是否和原有人员的补充、培训和流动同步进行?监管政策的专业化水准,直接取决于研究人员的专业化水准,这就要求监管队伍应该包含足够的经济、金融、法律方面的人才。在发展中国家,与其关注机构的分合问题,不如将监管仍置于央行的羽翼之下,而将精力更多地放在迫在眉睫的事情上,例如监管人
22、员的专业化上面,尤其是他们的专业素质、面对外部压力的独立监管精神和适宜的薪酬激励(Charles.Goodhart and Dirk Schoenmaker,1995) 。即使退一步讲,从香港、马来西亚和匈牙利等监管机构等的经验来看,监管机构内部监管实施部门和研究部门的设置应平行,并且政策研究和实施人员应定期轮换,使政策和实践相结合,保证监管的连续性和稳定性,避免以行政口号和行政行为代替持续有效的金融监管。如果机构独立的同时,人员仍从原金融工委、央行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抽调集中行政干部,那么机构独立和人才专业化集聚就可能出现落差。3、监管实施过程中,监管政策的实施是否能和监管对象自身的变迁同步进
23、行?如果被监管的银行体系仍沿袭传统的官本位激励机制,如果银行内部治理结构仍然不善且外部仍以利率管制为运行背景,如果专业协会等组织发育不全,如果存款性机构的经营仍然受地方政府的广泛影响,那么被监管对象因缺乏市场化而无法对监管政策作出足够的反应,而监管政策也可能难以感受到来自监管对象的反馈而不能及时调整。 因此,机构变动不是金融监管专业化的必要前提,我们必须审慎地反思原有监管为什么效能不佳的体制因素,并充分考虑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由于其特殊的经济环境、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的法律体制和抑制型金融体系本身的惯性对有效金融监管的种种制约(张俊喜,2001) ,否则不慎重的机构改革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央行
24、两种职能分离带来的好处。三、国际“机构分立”趋势和央行独立性近年来国际上的普遍趋势是将原属于央行的监管职能逐步分离出来,成立一个负责银行、证券和保险三大金融领域的合并式监管机构。中央银行和监管部门“机构分立”趋势是人们倾向于央行银监会分立模式的重要理由,并且被视为符合中国金融混业的前瞻性理由。有一些重要研究对国际三大金融监管模式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倾向于机构分立的政策建议。但如果我们仔细审视就不难发现,引发机构分立的制度变迁背景是,金融业的发展和变迁使得各业务功能界限越来越模糊,基于金融机构说的监管体系必须依据金融功能说予以重组,在央行已享有较高的独立性时,对央行过于“威权”(over-mig
25、hty bully)的忧虑,以及货币政策和监管政策存在着潜在利益冲突的忧虑与日俱增。而上述变迁背景在中国远未充分显见。我们以中国学者习惯的美国、德国、英国和日本为典型模式,对机构分立趋势和有效监管进行重新分析。 美国如何处理其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在1999年之前,美国对银行体系的监管是支离破碎的,其中对存款性金融机构承担主要监管职责的竟然有5家联邦级机构和一家州级机构、,其中联邦级监管机构有美联储(FRS)、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货币监理署(OCC)、储贷监理署(OTS)、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除货币监理署和储贷监理署在行政上隶属财政部外,其余3家则为独立的联邦政府机构。除了联邦级
26、的金融监管机构,由于美国实行双轨银行制,每个州又都设有自己的银行监管部门,通常称之为州银行(DFI),美国存款性机构往往处于联邦和州两级金融监管机构的双重监管之下。美国人对其金融监管体系是否应该整合的争论已经持续了60年,直到1999年美国参众两院通过1999年金融现代化法案后,金融监管的基本趋势才得以明确,该法赋予美联储对金融持股公司的监管权力,由于美国的金融机构已通过金融控股公司使得银行、保险、证券行业高度混业,这实际上是使得美联储成了能同时监管银行、证券和保险行业的唯一家联邦机构(金中夏,2001) 。因此美国金融监管的现实是正试图将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均集中到美联储去,而不是另设机构。应
27、该说,中国央行的机构设置和美联储有类似之处,目前也同样面临着多头监管的问题,银行的银行监管一司及二司、外汇局、金融工委和财政部等等,都部分地享有银行业监管的权力,可谓监管重叠和漏洞并存,就行使有效的金融监管而言,最紧迫者并非在央行之外另设机构,而在于丰富监管政策的体系性和强化监管措施研究,切实充实一线监管队伍并协调现场和非现场监管,既对商业银行实施有效监管,又避免因过于苛严的金融管制而使得商业银行无所适从。遗憾的是,目前人们更多地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寄托在另设机构上,而非上述更为基础的工作,也似乎忽略了美国长期以来就上述问题的争论以及最后美联储的身兼二任。如果将金融监管的有效性寄托在另设机构上,
28、银行监管就很可能在低水平上简单重复。 那么是否存在未来将金融监管职能从美联分离出去另设一个独立于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有这种可能性,但这将意味者美国金融监管体系的彻底更新,美联储曾经委托芝加哥期货交易委员会就金融功能说的角度,对未来新型金融监管架构进行探索,结果研究报告的结果是:应把现有的相互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合并成一个总统领导下的内阁部门,以使监管政策能够实现跨产品、跨市场、跨机构的协调,监管机构能够对其监管政策的成功与失败负责。未来独立于美联储的金融监管机构将包括一个联邦金融监管局、八个委员会和三个办公室,整合的对象不仅包括上述联邦和州的6个监管部门,甚至还包括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
29、、证券交易委员会(SEC)、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和养老金收益担保公司(PBGC)。此外,它还接管了联储监管银行和银行控股公司的职能,以及劳工部监管雇员退休收入保障计划(ERISA)的职能。这个研究报告中提议的独立于美联储的金融监管机构完全摒弃了现有的金融机构说而以金融功能说为其建构基础,显得十分超前,例如在这个金融监管框架下,银行和保险甚至被视做功能接近的金融机构而被纳入同一个委员会来管理。如果我们注意到多头分离的金融监管经过长达60多年的争论才逐渐纳入到以美联储为核心的统一监管中去的艰难,那么就不难看出,即使未来将金融监管从美联储重新独立出去,成立全新的超级金融监管机构是何等漫长的
30、过程。在学界倡议金融监管应该独立于央行时,德国可能是他们持上述观点的最好的范本。毕竟德国是最早建立独立于央行之外的综合金融监管机构的国家。在1961年,前联邦德国就通过了银行法,授权建立联邦银行监督局,它直接隶属于德国财政部,由于德国银行业可以同时经营证券和保险,银监局实际上就是一个综合金融监管当局。但我们不能不关注到,在当时金融监管之所以应独立于德意志银行,乃在于德意志银行是世界上最具独立性的中央银行之一,其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很少受政府干预。正是德意志银行拥有高度独立的货币政策决策权,人们才倾向于将监管职能从其中分离出来,以免央行权力太大,对德国经济影响力过于巨大。即便如德国那样将货币政策
31、和金融监管相分离的国度,银行法中仍然承认银监局的功能与德意志银行的功能密不可分。银监局自身缺乏分支机构,必须借助于央行的机构和网点才能有效实施金融监管,因此央行事实上广泛地参与银行监管。德国银监局负责制定和颁布联邦政府有关监管的规章制度,防止滥用内部信息、不定期收集监管信息以及监督重大的股权交易等。央行负责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的监管。在涉及银行资本金和流动性的重大政策问题上,银监局更需征得央行的同意。观察以上情况,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德国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分离并不彻底,在监管职能上央行仍是主角,在监管机构上有银监局独立于央行之外,这是作为对权力过大的央行的某种制衡。相比较之下,中国央行是否享有某种程
32、度的独立性,尤其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呢?答案基本是否定的,近年来央行更多地扮演着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和温和修正者的角色,而非决策者角色,这是长期以来显而易见的事实,货币政策决策更多地源自于国务院的综合考虑和意愿,因此所谓央行的角色冲突可能在德国央行身上是存在,而在中国央行身上可能色彩相当弱,因为央行制定货币政策独立性方面的缺陷使得它其实基本不扮演货币政策决策者的角色,自然所谓角色冲突就也无从谈起。此外德国银监局是从属财政部的,而在中国如果采取类似思路,可能后果相当严重。此外,中国几乎面临和德国完全类似的问题,即银监会如何才能行使有效的金融监管?如果采取类似德国的模式,靠央行的分支机构来完成
33、,那么银监会在实际职能执行时仍然依附于央行;如果采取自上而下设立完全平行于央行的自身分支机构,那么这个开支是相当庞大的。目前那些将金融监管机构独立于央行以外设置的国家,一般要通过立法解决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并通过向监管对象收费解决资金来源问题。但是发展中国家很难做到这点。那么姑且不考虑机构铺开的成本,央行和银监会各自作为多层级的管理机构,进行工作沟通、协调和信息共享的难度显而易见。一个强而独立的央行或者可能存在将金融监管职能分离出去的必要性,但一个弱而从属的央行是否具有这样的必要性尚未可知。值得注意的是,在1999年欧洲中央银行成立以后,德意志银行失去了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功能,只能对欧洲中央银行
34、的货币政策提出分析和建议,并执行欧洲中央银行的决定。上述变化迫使德国政府重新考虑央行和银监局从机构上相分离的必要性,并设想将报监局划入央行,同时减少分行数量,将决策权向央行总行集中。由此可见,如果央行失去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那么角色冲突就基本不存在,在其外设立独立的金融监管机构的必要性理由就显失充分。与德国情况相反的例子是英国和日本。就英国的情况来讲,长期以来,英格兰银行是发达国家的中央银行中少数不具备独立制定货币政策权利的中央银行之一,相应地,在金融监管方面,也由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银行业和证券业的监管,此外金融行业自律组织在监管中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随着英格兰银行独立性的逐
35、渐增强和金融混业趋势的抬头,英国的金融改革也随之展开。19<#004699'>98年英格兰银行法赋予英格兰银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能力,同年,英国政府将英格兰银行、证券投资委员会和其它金融自律组织合并,成立了独立于英格兰银行之外的金融监管机构,即金融服务局。在2000年6月英国通过金融市场与服务法案,从法律上进一步确认了上述金融监管体制的改变。就日本的情况来讲,传统上日本的金融监管以大藏省为主,大藏省负责金融政策、法规的制定,批准金融机构的准入并对其监管。相应地日本银行也并不具备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这个权力实际上也由大藏省掌握,当然日本银行也参与对金融机构的日常监管。日本
36、银行相对于大藏省的积弱地位所带来的问题,已经集中地体现在迄今为止难有起色的日本银行体系中,至少迄今为止这种制度安排受到的批评远远多于赞誉。19<#004699'>98年,日本对金融监管体系进行了所谓“大爆炸”的重大改革,就央行和金融监管的角度观察,最显著的变化在三点,一是大藏省对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的全面淡出;二是通过新的日本银行法赋予日本银行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职能,但强调日本银行应履行金融监管的职责;三是成立了独立于日本银行之外的金融监管厅,统一负责对各类金融机构的监管。如果我们将英国和日本的上述变化作为与德国相反的例子,那么经验分析的结论就更为明确:如果一国试图顺应金融混
37、业的基本趋势,将分离的金融监管机构整合为一并独立于央行,那么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就必须得以加强,否则货币政策决策,实施,监管就可能脱节。更富有戏剧性的是,即使英国和日本将央行和金融监管分立之后,金融监管职能从央行的剥离仍然是不充分甚至几乎不可能的。从英国新的金融监管体制的实际运营情况看,一则英格兰银行仍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必须为不具备创造流动性的金融服务局补充此职能;二则英格兰银行长期积累的金融监管数据和经验是金融服务局所不可或缺德的,结果根据19<#004699'>98年英格兰银行法和英格兰银行与财政部和金融服务局的备忘录,英格兰银行仍需负有维护整个金融系统稳定的职责。为
38、此,英格兰银行内部新设了金融稳定委员会和金融市场稳定局,类似的情况发生在日本,19<#004699'>98年日本银行也在进行机构重组中成立了金融检查局,负责对金融机构的监管及与此相关的金融稳定工作。从实践来看,此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以新设机构承担“金融稳定”职能似乎仍属金融监管。 更有意思的是,所谓央行内部的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角色冲突外部化之后,外部冲突的隐患仍然存在,人们原先担忧央行因角色冲突而对金融监管难以中立,所以鼓吹分离;分离之后却发现一旦央行、金融监管当局和财政部就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应采取的措施产生分歧并争执不下时,谁来最终决策?在原先不分离模式下,央行内部再激烈
39、争吵也必须最终给出答案,这是央行身兼二任时必须履行的义务;在新型分离模式下,三方不能妥协并给出答案时,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纠纷被提交到内阁来处理。有的学者可能忽略了央行和金融监管就职能上彻底分离的技术障碍和行政障碍,认为央行所负的仅仅是对金融机构的“检查权”, 央行只根据场内外检查和实地调研得到的实际情况来决定宏观的货币政策走向,而不对具体的金融机构承担微观的监管责任。即使监管方面出现问题,中央银行也不需要承担具体责任。这样央行“检查权”似乎就与金融监管彻底无涉了(魏加宁,2003) 。这种看法,和德国央行与银监局的关系,以及英、日央行在与银监分离后继续依法承担的金融稳定职责完全相悖,从理论和实
40、践上看均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如此情况就清楚了:对转轨经济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银行业居于垄断地位而资本市场欠发达的国家而言,成立专门的全能金融监管机构是得不偿失(Alex Fleming, and Michael Taylor,1999) 。央行和金融监管从机构上相分离的动因,往往是金融混业的推动,中国是否已经面临巨大的金融混业压力,并将央行-银监分离模式作为未来确立统一金融监管机构的前奏?如果不是,那么这种分离的必要性就不紧迫。此外中国试图在不改善央行独立性的同时,采取央行、银监会的独立模式,那么不仅因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连续性及央行天然地具有的最后贷款人职责,而使金融监管难以从央行彻底分离,也可
41、能使新生的外部角色冲突并不对原先的内部角色冲突享有任何改进的优势,并最终造成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两项职能向国务院的事实上的集中。从目前的理论和实践上看,要评价分立模式下央行或监管部门的有效性及其效率都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对赞成或否定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的纷争也不少,但即使是赞成综合性金融监管模式的学者,也倾向于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前提条件(Charles.Goodhart,2002) 。因此,以混业和机构分立是国际趋势,并将其作为中国目前应该采取类似模式的看法,和中国金融业的实际发展状况来说,的确显得相当“前瞻”。 四、若干简要结论至此我们可以简要地将讨论的结论做如下总结:关于央
42、行在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时,兼具金融监管职能的角色冲突问题,角色冲突的确存在,并且可能引发央行的通货膨胀倾向,以及商业银行对中央银行的“监管捕获”效应。但通过机构分立将角色冲突外部化,并不能使监管职能也同步分立,并带来央行和监管机构的协调难题,以及央行在行使最后贷款人职责时的非中立性姿态。关于央行的角色冲突和监管弱化,和央行享有高度的货币政策制定和执行权央行是密切相关的,正是担心央行过于“威权”,所以才出现了将金融监管职能从央行分离的趋势。一国央行如果货币政策的决策和实施独立性较弱,或者央行乃行使金融监管的高度离散的机构中的一环的话,那么就意味着或者必须增强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然后将金融
43、监管职能剥离;或者必须首先整合离散的金融监管职能,然后才有可能进行金融监管机构的分立。关于央行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宏观性,以及行使金融监管的微观性反差,的确可能妨害了金融监管的专业化程度。但经验分析表明金融监管的专业化程度首先表现为金融监管理念、政策、职能和传导机制的专业化,然后才是监管机构的专业化,脱离监管职能的专业化提升进行的机构专业化,很可能导致金融监管效能的低水平重复。关于央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分立的国际趋势,上述趋势的确存在,这种趋势的动因在于银行、证管和保险行业的混业加速,使得基于金融机构说的分业监管框架相对滞后。因此机构分立的前提是该国已面临巨大的金融混业压力。目前对机构分立的效能尚
44、存争议,但即使是倾向于综合性金融监管模式者,也认为发展中国家不具备综合性金融监管机构的前提条件。 王 君:“金融监管机构设置问题的研究”,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1期。 Joseph.Haubrich:“Combining Bank Supervision and Monetary Policy”,Journal Economic Commentar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November,1996. Charles.Goodhart:“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Banking Supervision”,
45、Financial Markets Group Special Papers,No. sp0127, Oct, 2000. Xavier.Freixas:“Optimal Bail-Out, Conditionality and constructive ambiguity”, Financial Market Group Discussion Paper,NO. 237,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1999. 王 君:“银行监管应当专业化”,财经2002年2月5日。 陈工孟,林朝华:“银行监管脱离央行适合中国吗?”,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报告,2001年12月第37
46、期。 Charles.Goodhart and Dirk Schoenmaker:“Should the Functions of Monetary Policy and Banking Supervision Be Separated?” Oxford Economic Papers, Vol. 47 (4), 1995. 张俊喜:“央行是否应该有监管职能?”金融研究2001年第12期。 金中夏:“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比较与启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年第4期。 魏加宁:“成立银监会加大央行独立性”,财经界2003年第2期。 Alex Fleming, and Michael Taylor:
47、“Integrated Financial Supervision: Lessons from Northern European Experience”,World Bank Working Paper No.2223, November 1999. Charles.Goodhart:“Measuring Performance in Central Banks and Financial Regulatory Agencies”,Workshop of The Emerging Framework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8-12 September 8-12, 2002.
- 温馨提示:
1: 本站所有资源如无特殊说明,都需要本地电脑安装OFFICE2007和PDF阅读器。图纸软件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压缩文件请下载最新的WinRAR软件解压。
2: 本站的文档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图纸等,如果需要附件,请联系上传者。文件的所有权益归上传用户所有。
3.本站RAR压缩包中若带图纸,网页内容里面会有图纸预览,若没有图纸预览就没有图纸。
4. 未经权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将文件中的内容挪作商业或盈利用途。
5. 装配图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保护处理,对用户上传分享的文档内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编辑,并不能对任何下载内容负责。
6. 下载文件中如有侵权或不适当内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立即纠正。
7. 本站不保证下载资源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时也不承担用户因使用这些下载资源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