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落脚城市2005
落脚城市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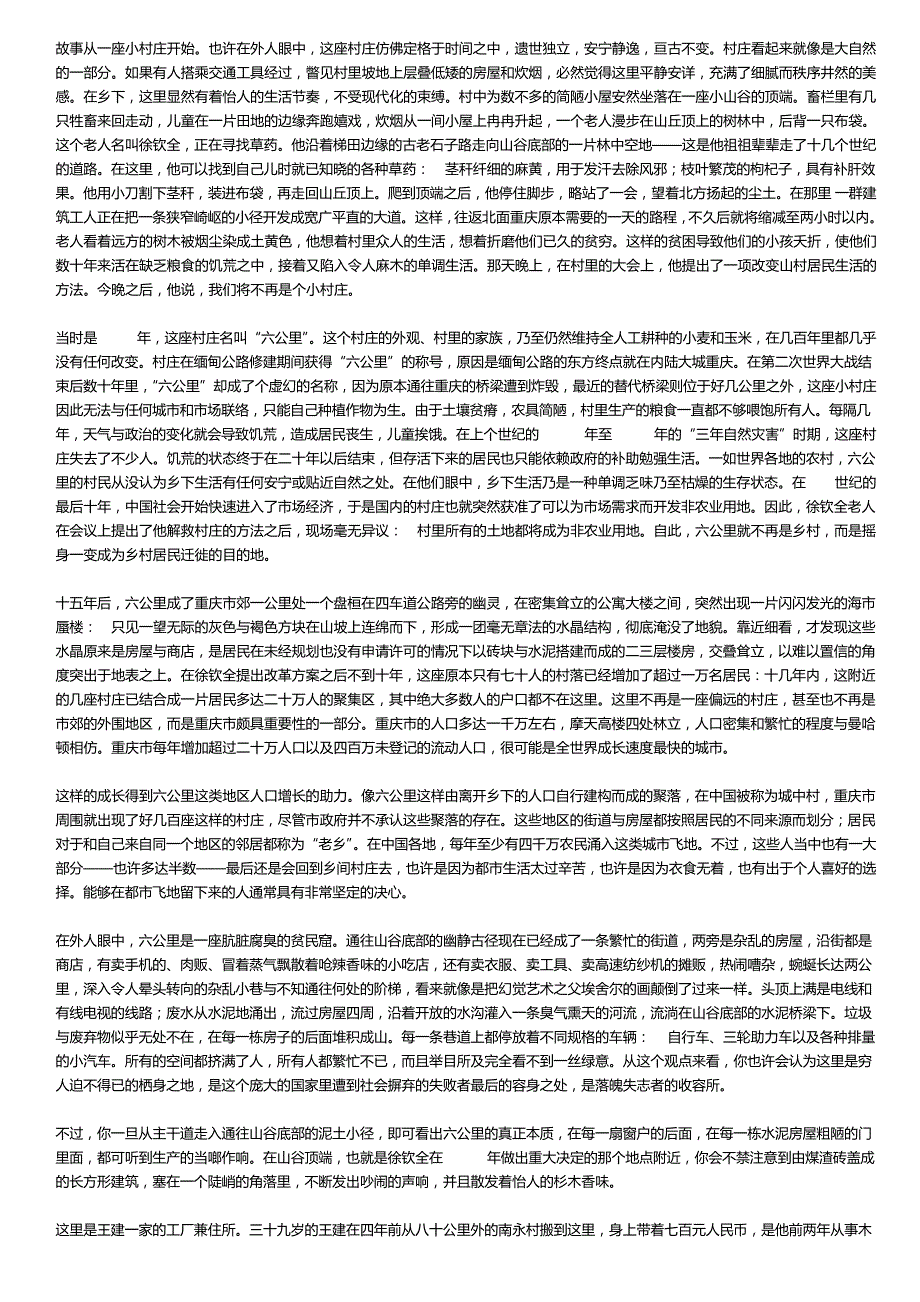


《落脚城市2005》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落脚城市2005(3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故事从一座小村庄开始。也许在外人眼中,这座村庄仿佛定格于时间之中,遗世独立,安宁静逸,亘古不变。村庄看起来就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如果有人搭乘交通工具经过,瞥见村里坡地上层叠低矮的房屋和炊烟,必然觉得这里平静安详,充满了细腻而秩序井然的美感。在乡下,这里显然有着怡人的生活节奏,不受现代化的束缚。村中为数不多的简陋小屋安然坐落在一座小山谷的顶端。畜栏里有几只牲畜来回走动,儿童在一片田地的边缘奔跑嬉戏,炊烟从一间小屋上冉冉升起,一个老人漫步在山丘顶上的树林中,后背一只布袋。这个老人名叫徐钦全,正在寻找草药。他沿着梯田边缘的古老石子路走向山谷底部的一片林中空地这是他祖祖辈辈走了十几个世纪的道路。在这里
2、,他可以找到自己儿时就已知晓的各种草药:茎秆纤细的麻黄,用于发汗去除风邪;枝叶繁茂的枸杞子,具有补肝效果。他用小刀割下茎秆,装进布袋,再走回山丘顶上。爬到顶端之后,他停住脚步,略站了一会,望着北方扬起的尘土。在那里,一群建筑工人正在把一条狭窄崎岖的小径开发成宽广平直的大道。这样,往返北面重庆原本需要的一天的路程,不久后就将缩减至两小时以内。老人看着远方的树木被烟尘染成土黄色,他想着村里众人的生活,想着折磨他们已久的贫穷。这样的贫困导致他们的小孩夭折,使他们数十年来活在缺乏粮食的饥荒之中,接着又陷入令人麻木的单调生活。那天晚上,在村里的大会上,他提出了一项改变山村居民生活的方法。今晚之后,他说,
3、我们将不再是个小村庄。当时是 1995年,这座村庄名叫“六公里”。这个村庄的外观、村里的家族,乃至仍然维持全人工耕种的小麦和玉米,在几百年里都几乎没有任何改变。村庄在缅甸公路修建期间获得“六公里”的称号,原因是缅甸公路的东方终点就在内陆大城重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数十年里,“六公里”却成了个虚幻的名称,因为原本通往重庆的桥梁遭到炸毁,最近的替代桥梁则位于好几公里之外,这座小村庄因此无法与任何城市和市场联络,只能自己种植作物为生。由于土壤贫瘠,农具简陋,村里生产的粮食一直都不够喂饱所有人。每隔几年,天气与政治的变化就会导致饥荒,造成居民丧生,儿童挨饿。在上个世纪的 1959年至 1961年的
4、“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这座村庄失去了不少人。饥荒的状态终于在二十年以后结束,但存活下来的居民也只能依赖政府的补助勉强生活。一如世界各地的农村,六公里的村民从没认为乡下生活有任何安宁或贴近自然之处。在他们眼中,乡下生活乃是一种单调乏味乃至枯燥的生存状态。在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社会开始快速进入了市场经济,于是国内的村庄也就突然获准了可以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非农业用地。因此,徐钦全老人在会议上提出了他解救村庄的方法之后,现场毫无异议:村里所有的土地都将成为非农业用地。自此,六公里就不再是乡村,而是摇身一变成为乡村居民迁徙的目的地。十五年后,六公里成了重庆市郊一公里处一个盘桓在四车道公路旁的幽灵,
5、在密集耸立的公寓大楼之间,突然出现一片闪闪发光的海市蜃楼:只见一望无际的灰色与褐色方块在山坡上连绵而下,形成一团毫无章法的水晶结构,彻底淹没了地貌。靠近细看,才发现这些水晶原来是房屋与商店,是居民在未经规划也没有申请许可的情况下以砖块与水泥搭建而成的二三层楼房,交叠耸立,以难以置信的角度突出于地表之上。在徐钦全提出改革方案之后不到十年,这座原本只有七十人的村落已经增加了超过一万名居民:十几年内,这附近的几座村庄已结合成一片居民多达二十万人的聚集区,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户口都不在这里。这里不再是一座偏远的村庄,甚至也不再是市郊的外围地区,而是重庆市颇具重要性的一部分。重庆市的人口多达一千万左右,摩天
6、高楼四处林立,人口密集和繁忙的程度与曼哈顿相仿。重庆市每年增加超过二十万人口以及四百万未登记的流动人口,很可能是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城市。这样的成长得到六公里这类地区人口增长的助力。像六公里这样由离开乡下的人口自行建构而成的聚落,在中国被称为城中村,重庆市周围就出现了好几百座这样的村庄,尽管市政府并不承认这些聚落的存在。这些地区的街道与房屋都按照居民的不同来源而划分;居民对于和自己来自同一个地区的邻居都称为“老乡”。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四千万农民涌入这类城市飞地。不过,这些人当中也有一大部分也许多达半数最后还是会回到乡间村庄去,也许是因为都市生活太过辛苦,也许是因为衣食无着,也有出于个人喜好
7、的选择。能够在都市飞地留下来的人通常具有非常坚定的决心。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通往山谷底部的幽静古径现在已经成了一条繁忙的街道,两旁是杂乱的房屋,沿街都是商店,有卖手机的、肉贩、冒着蒸气飘散着呛辣香味的小吃店,还有卖衣服、卖工具、卖高速纺纱机的摊贩,热闹嘈杂,蜿蜒长达两公里,深入令人晕头转向的杂乱小巷与不知通往何处的阶梯,看来就像是把幻觉艺术之父埃舍尔的画颠倒了过来一样。头顶上满是电线和有线电视的线路;废水从水泥地涌出,流过房屋四周,沿着开放的水沟灌入一条臭气熏天的河流,流淌在山谷底部的水泥桥梁下。垃圾与废弃物似乎无处不在,在每一栋房子的后面堆积成山。每一条巷道上都停放着不
8、同规格的车辆:自行车、三轮助力车以及各种排量的小汽车。所有的空间都挤满了人,所有人都繁忙不已,而且举目所及完全看不到一丝绿意。从这个观点来看,你也许会认为这里是穷人迫不得已的栖身之地,是这个庞大的国家里遭到社会摒弃的失败者最后的容身之处,是落魄失志者的收容所。不过,你一旦从主干道走入通往山谷底部的泥土小径,即可看出六公里的真正本质,在每一扇窗户的后面,在每一栋水泥房屋粗陋的门里面,都可听到生产的当啷作响。在山谷顶端,也就是徐钦全在 1995年做出重大决定的那个地点附近,你会不禁注意到由煤渣砖盖成的长方形建筑,塞在一个陡峭的角落里,不断发出吵闹的声响,并且散发着怡人的杉木香味。这里是王建一家的工
9、厂兼住所。三十九岁的王建在四年前从八十公里外的南永村搬到这里,身上带着七百元人民币,是他前两年从事木工攒下的积蓄。他租下一个小房间,捡了一些废弃的木料和铁料,然后开始以手工制作传统的中式洗浴木桶。这种木桶颇受新兴中产阶级的喜爱。他花了两天时间做出第一批木桶,然后卖了出去,每个木桶能赚五十元人民币。一年后,他赚的钱已够他买些电动工具和一间较大的工作室。他把老婆、儿子、还有儿媳妇以及仍在襁褓中的孙子一起接了过来。他们睡觉、煮饭、洗衣、用餐都在工作室后方一个没有窗户的空间里,只用一张塑胶帘布隔开。比起他们当初在村里勉强居住的小屋子,这个空间不但更拥挤,也更缺乏隐私。尽管如此,却没有人想要回乡下去:这
10、里虽然肮脏狭小,生活却比乡下好得多。“在这里,你只要找对了谋生方式,就可以让你的子孙获得成功的机会在乡下,你只能努力填饱肚子。”王先生一面用一条铁皮带子拴住木桶,一面用连珠炮般的四川方言说着,“我们那个村头和我一样离乡背井的人,我觉得差不多有五分之一都是个人在创业。而且,基本上全部人都走了只有老人还留在那里,已经成了空村子了。”王先生和他的太太仍然会把收入的三分之一寄回村里,供养他们仍然健在的父母。一年前,他在六公里买下了同一条路上的一家餐厅让他儿子经营。老王的获利空间很小,因为竞争非常激烈:重庆还有另外十二家洗浴木桶工厂,其中一家也在六公里。“我的工厂产量最高,”他说,“可是利润不一定是最高
11、的。”因此他们还得存许多年的钱,并且祈求洗浴木桶业的热潮不退,才有能力买下自己的公寓,把孙子送上大学,并且举家离开六公里。不过,等到他们梦想成真的那一天,说不定六公里也已经成了他们梦想中的城市。这座山谷看起来犹如一幅灰色的立体派画作,草草搭建而成的水泥建筑里藏着许许多多在政府记录上并不存在的微小企业。在木桶工厂的同一条街上,可以见到一个大型冷藏库,一家粉末颜料搅拌厂,一家工厂以五六部大型机器输出刺绣团,另一家生产电动马达线圈,还有一个地方酸味刺鼻,许多十七八岁的小工人正弯着腰操作塑封机,制作吹气海滩玩具。这里有着各式各样的家庭工厂,制作橱窗道具、塑钢窗户、工业用空调管,生产廉价木质家具、木质装
12、饰床架、高压变压器、电脑车床加工而成的摩托车零件,以及不锈钢抽油烟机。这些以亚洲各地为主要销售市场的工厂全都创立于近十多年,老板不是外来的乡村移民,就曾是第一波乡村移民的员工。在每一栋素面的水泥方块建筑里,都可以听到同样的故事:从外地搬迁而来,努力奋斗,供养家人,认真储蓄,规划未来,仔细盘算自己的每一步。住在六公里的所有居民,还有这个地区的十二万人口,都是 1995年以来移入的村民。这里虽然肮脏、拥挤、生活困苦,而且他们经常把子女和老人留在乡下,但他们只要在这里撑过头几个月,就会决定留下来长期奋斗,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才有希望。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很长一段时间的自我否定以及极度贫困的生活。几乎所有人
13、都寄钱回家供养村里的老人,再存一点钱准备让孩子日后到城里接受教育,而这几乎就用掉了他们全部的收入。所有人都不断盘算着自己的前途,一方面是乡下让人难以忍受的贫困生活,另一方面是城市生活难以负担的开支,同时也盼望着有一天能时来运转,突破这两方面的窘境。换句话说,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他们迁徙过程的落脚。如同世界各地都市外围的新兴区域,六公里也具有一套特定的功能。这里不只是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种重要活动的目的都在于把这些村民乃至整座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带进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核心,让他们得以接受教育和适应文化,融入主
14、流社会,享有可长久的繁荣生活。落脚城市不但聚集了处于过渡期的居民外来人口一旦到了这里,即可转变为“核心”的都市人,在社会、经济与政治等方面都得以在都市里享有可长久的前途而且本身也是处于过渡时期的地区,因为这里的街道、住宅,还有居住在这里的家庭,有一天都将成为核心都市的一部分,不然就是在追求目标的路途中败下阵来,陷入贫穷的深渊,或是遭到捣毁拆除。落脚城市和其他都会地区有着极为鲜明的差异,不只因为这里住的都是外来的乡村人口,也不只因为这里的市容充满了临时拼凑的色彩,总是变化不休,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条街道、每一间住家和每一个工作场所,都不断联系着两个方向。一方面,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
15、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通不曾止息,从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活动得以发生,也让村里的老年人得以照顾、年轻人得以受教育、村庄本身也得以拥有建设发展所需的资金。另一方面,落脚城市也和既有城市具有重要而深切的联系:其政治体制、商业关系、社会网络与买卖交易等一个个的立足点,目的在于让来自乡村的新进人口能够在主流社会的边缘站定脚步不论这样的立足有多么如履薄冰从而谋取机会把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推向都市核心,以求获得社会的接纳,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六公里生产许多产品、贩卖许多产品,也容纳了许多人口,但这许许多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活动,都有着一项核心的目标,一个共同的使命。六公里是一座落脚城市。在城市的外围地区
16、,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中心。从工厂聚集的山谷底部沿着蜿蜒的碎石路走上一小段陡坡,即可来到山谷顶端,而这里的水泥建筑更是密集。如果你走进一家小餐馆后面的巷子,在高墙围绕下穿越有如迷宫般的隧道与狭隘走道,即可抵达一座小小的灰色天井。这里是嘈杂混乱的贫民窟当中一个静僻的地点,摆着一张小桌,周围排列着木头矮凳。在这里,空气中弥漫着川菜的辛辣气味,不时可听到远处隐隐传来的车声、婴儿的啼哭声、吼叫号令的声音,还有广播声。桌子旁蹲伏着一个老人,身穿传统的青布外套和一双破旧的帆布鞋,头上戴着耐克棒球帽。他身边放着一顶斗笠,里面装满了他采集的草药。他采集这些草药的地点在山谷另一端一片鲜为人知的绿地,就在那堆五层楼高
17、的垃圾山后面。原本的林间空地已经大半都被那堆垃圾山淹没了。这个老人就是徐钦全,草药采集者及村庄元老。他仍住在六公里的中心,地点和当初一模一样,村庄转为都市为他带来了大量财富:他靠租房收入,买下了好几间楼层公寓供家里人居住。这些公寓一间就至少值七万五千美元(2007年),相当于一名城市白领近十年的收入。他独自住在这里,靠近他的草药生长地。这座村庄仍由原本的居民集体拥有,而且在法律上也仍然属于村庄。也就是说,除了这间房子以外,其他数以百计的住宅都不完全属于屋主所有,尽管许多人都向村里买下了产权证书,也靠着买卖赚进了不少利润。在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下,租金与非官方土地价格都跟着水涨船高,于是这些身为房东
18、的乡村居民也就得以通过出租、转租以及房产投机买卖而获得财富,而且这些资本活动都不算正式的交易行为,也不必纳税。他们经常利用藉此赚得的财富创业。市政府只要愿意,随时都可将这整个地区夷为平地,把十二万居民全部驱离,或是安排他们住进公寓楼,隔壁就有国营的成衣工厂,环境清洁舒适。中国已经对数以百计的这类地区采取过这种做法,毫不留情的摧毁许多家庭在都市边缘投注一切所得来的生活与经济基础。六公里的创立者自信他们至少还有十年的时间才会遭遇同样的下场。重庆市一位人大代表曾告诉我说,他们有一天会把这座大都市转变为没有贫民窟的城市,把这些破烂的聚落改建成整洁的工厂园区及私人公寓。不过,他也说虽然他们希望城市化的速
19、度愈快愈好,但如果要吸收这样的成长率所带来的庞大人口,这些高度密集的非正式聚落必然又不免出现人口的指数型成长。重庆周围虽然每天都有数千栋开发商建造的商业住宅楼正在施工,但住宅供给的预算却还比不上涌入的人口数量。而且,官方仍然把这些移入的乡村人口排除在保障性的住宅供给对象之外,除非他们能赚到足够的钱去购买一套商品房。落脚城市不是一种暂时性的异常现象:在中国的内陆城市,这些扮演落脚城市角色的村庄虽然不受承认,却已经成了城市的成长计划、经济活动以及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的房客通常都一心想成为城里人,但只有极少数能够实现梦想。”徐先生对我说,他的女儿在一旁准备着端午节的丰盛午餐。“他们赚的钱
20、通常不够储蓄,生活支出对他们来说也变得太高了。除非这里的状况出现改变,否则他们有许多人都会不得不搬回去。我们都不想再当农民,现代中国也要我们成为城里人,但这个目标已经变得很难达成。”的确,六公里的许多居民都像三十六岁的王珍蕾与三十四岁的舒伟东夫妇一样,晚上就睡在长三公尺、宽两公尺的房间里,隔间的石膏板垂挂在水泥天花板下方半公尺处的木板条上。这是一幢夫妻宿舍,里面隔出了十几个相似的房间,整幢建筑则是颤巍巍地耸立在一条恶臭的溪流旁。唯一的一扇窗户不但上了锁,而且还遮盖起来,只剩下顶端一条六十公分宽的开口,室内的照明来自赤裸悬挂的白炽灯泡。他们一天有十个小时,而且经常在周末,都待在隔壁的一间水泥房间
21、里,在工作桌前缝制着衣物。这个房间没有多余的陈设,除了墙面上沾满线头之外,就只有一部彩色电视不停播放着连续剧。这家工厂共有三十张缝纫机,老板在 1996年从一座偏远的乡村搬到六公里。他自己原本也是个成衣工人,开这家工厂之后对员工按件计酬,因此他的员工一个月的薪水介于两百至四百美元之间。宿舍是免费提供的(不是所有的工厂都有这种福利)。除了六公里的街道之外,他们并未真正见识过重庆这座大都市。每个月,他们留下四十五美元的伙食费和三十美元的零用钱,其他的薪水全部寄回村里,供养他们女儿的中学学费及生活费,也供养帮他们带女儿的父母。从 1993年开始,他们夫妇俩曾有十一年的时间都在深圳,那里的工人宿舍比较
22、现代化,比较不那么幽闭。那座工业城位于珠江三角洲,在重庆以南一千五百公里处,许多成衣工厂为西方企业代工制造产品,不仅工作条件比较好,薪酬也比较高。不过他们却发现了一大缺点:深圳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不论他们怎么努力存钱,还是永远在深圳买不起一套房子。像六公里这样的贫民窟住宅是他们唯一可能买得起的选择,但在深圳那座特区城市里却没有这样的地方。此外,他们在深圳只有每年春节才能见到心爱的女儿一面。简言之,在深圳没有未来。经过一番痛苦的取舍之后,他们开始向北搬迁。这样,他们即可离家人近一点,而且女儿也说不定未来有机会到城市生活:不过,他们付出的代价则是大半辈子都得在孤独阴暗的深渊里工作。如同这里以及世界各地的许多人,他们赌上自己的一生,为的就是让儿女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不过,他们也知道这项赌注的胜算只有一半,甚至连一半都没有。
- 温馨提示:
1: 本站所有资源如无特殊说明,都需要本地电脑安装OFFICE2007和PDF阅读器。图纸软件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压缩文件请下载最新的WinRAR软件解压。
2: 本站的文档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图纸等,如果需要附件,请联系上传者。文件的所有权益归上传用户所有。
3.本站RAR压缩包中若带图纸,网页内容里面会有图纸预览,若没有图纸预览就没有图纸。
4. 未经权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将文件中的内容挪作商业或盈利用途。
5. 装配图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保护处理,对用户上传分享的文档内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编辑,并不能对任何下载内容负责。
6. 下载文件中如有侵权或不适当内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立即纠正。
7. 本站不保证下载资源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时也不承担用户因使用这些下载资源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