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我的喊声来到你的身边-民大学文学院
让我的喊声来到你的身边-民大学文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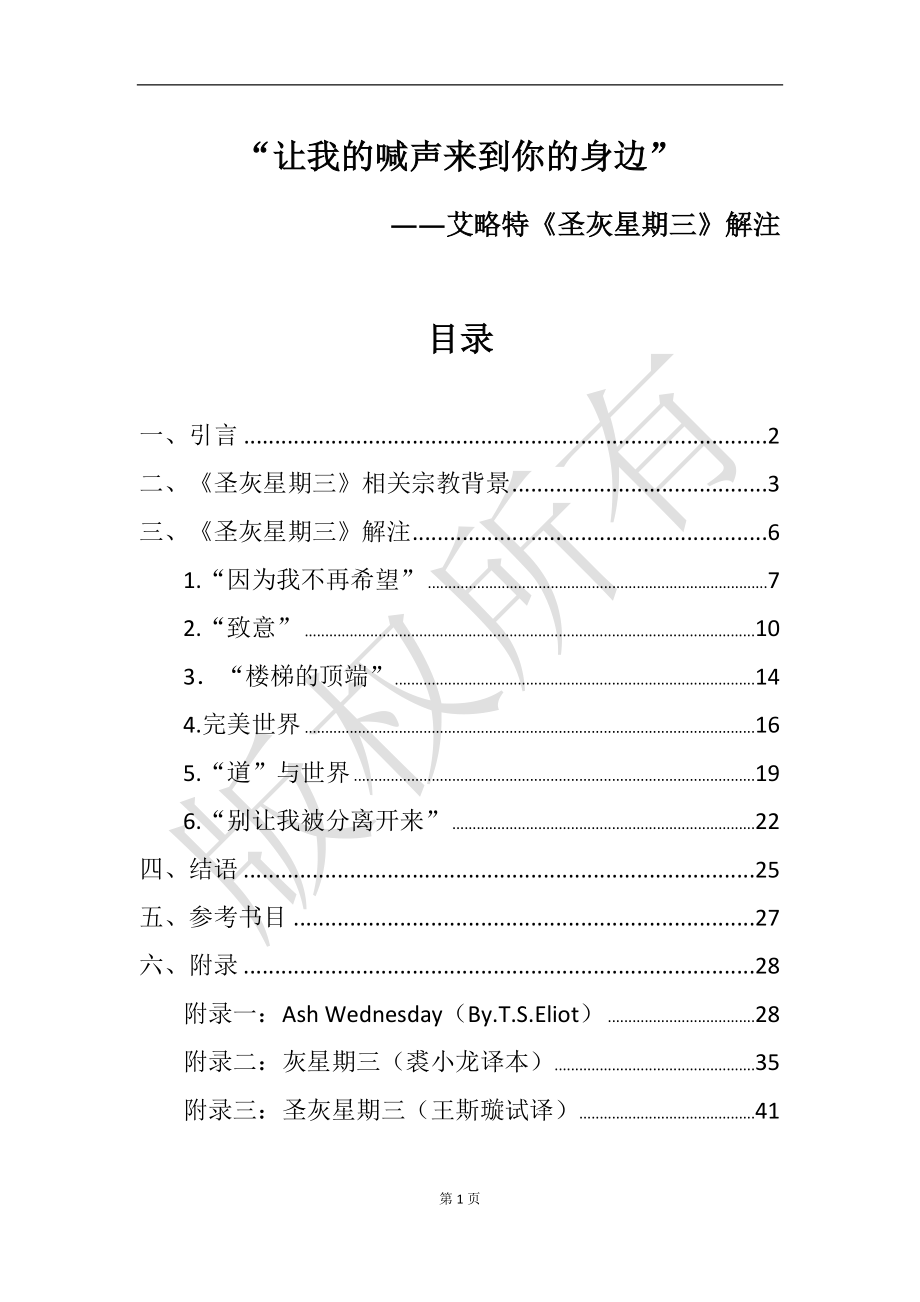


《让我的喊声来到你的身边-民大学文学院》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让我的喊声来到你的身边-民大学文学院(47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让我的喊声来到你的身边” 艾略特圣灰星期三解注目录一、引言2二、圣灰星期三相关宗教背景3三、圣灰星期三解注61.“因为我不再希望”72.“致意”103“楼梯的顶端”144.完美世界165.“道”与世界196.“别让我被分离开来”22四、结语25五、参考书目27六、附录28附录一:Ash Wednesday(By.T.S.Eliot)28附录二:灰星期三(裘小龙译本)35附录三:圣灰星期三(王斯璇试译)41“让我的喊声来到你的身边” 艾略特圣灰星期三解注【摘要】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圣灰星期三乃艾略特最终转向天主教的宣言,一个全新诗歌时期也就此开始。本文对诗人的宗教信仰历程进行梳理,在此基础上通过
2、圣经、但丁的神曲、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荷马史诗等对圣灰星期三进行注解,以超脱、告诫、苦行、补赎、放弃、仁爱为线索,试图解读诗中灵魂的忏悔和历练、以及艾略特对于自身的全新视角的审视,进一步理解艾略特晚期文学创作风格,对文学和宗教关系进行初步探究。【关键词】艾略特 圣灰星期三 解注 文学 宗教一、引言从荒原到四个四重奏,艾略特的诗歌创作中的诗意和诗技发生了明显改变,他努力将诗歌格调和技艺从经验主义的层面提升至个人精神意识。如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所言:“诗歌不再关注于外部世界、寻求各种方式尖刻地阐释和重复表达那空虚、孤寂和荒芜,而是把诗歌重心由人的外部世界转入
3、深思所谓确定而隐秘的个人经验。他缩小了视野,撤回至内心,全心全意专注于另一种强烈。早期诗歌关于忧虑和恐惧的强烈继而被深思冥想所取代。” Helen Gardner, The Art of T. S. Eliot, London: the Crescent Press, 1949, p.100.圣灰星期三无疑是这个转变阶段中最重要的作品,浓郁的宗教气息也标志着艾略特最终转向天主教。许多读者和评论家甚至感觉到圣灰星期三和荒原创作的不连贯性,一个全新诗歌时期就此开始。康拉德艾肯曾赞扬这首诗是“艾略特先生所有诗歌中最美的” 陈庆勋著,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页。作为艾略特
4、诗歌生涯中一个新的声音和新的姿态,圣灰星期三在国外受到很多学者、评论家的关注,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首诗的重视远远不够。裘小龙的四个四重奏首次翻译圣灰星期三,并对其中诸多意象进行了注解,遗憾的是颇为粗略。目前,国内针对性研究圣灰星期三的论文仅有两篇:其一是刘会、何江胜的中的原型意象解读 刘会、何江胜,中的原型意象解读,长江师范学院学报第24卷,2008年7月第4期。,通过诗歌中几个主要意象“花园”、“枯骨”、“鹰的翅膀”、“夫人、修女”初步解读了诗人的感情经历;其二是张剑的:“古老的激情” 张剑著,T.S.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解读,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82页。,通过对诗文中“衰老的
5、老鹰”、“崇高的梦幻”、“沙漠里的花园”的解读,联系艾略特和但丁在创作上的关系,探究了圣灰星期三中灵魂的煎熬和折磨。其中,他关于“艾略特的忏悔看上去不完全是真诚的(sincere),而仅仅是例行成规(routine)” 张剑著,T.S.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解读,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84页。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哈罗德布隆姆(Harold Bloom)在论及圣灰星期三时确实也有过类似说法,认为这首诗是“有关天主教的悖论的一个简单的、极其机械的目录,作为念珠游戏它是可以的,但作为想象的意义它就不行了。” 转引自:张剑著,T.S.艾略特:诗歌和戏剧的解读,外国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6、年,第82页。但笔者认为圣灰星期三中自始自终贯穿着某种永恒的时刻灵魂的变幻莫测,是艾略特对于自身的一个全新视角的审视。它为洞察灵魂提供了一个非凡的解释,同样在这种求解过程中通过一段艰难的朝觐之旅。“灵魂在追求新生中交替感受和经历的绝望、怀疑、希望和欢乐阶段。” (英)托斯艾略特著,艾略特文学论文集,李赋宁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0年,第4页。这个过程即是艾略特在一颗小小的灵魂一诗中写道的“从上帝的手中遣出,那单纯的灵魂。” (英)T. S.艾略特著,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若执意要判定诗人或诗中灵魂并无表面上那样虔诚和卑微,不免是对诗人痛苦灵魂探索的曲解。
7、联系艾略特的宗教信仰发展之路,清晰可见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圣灰星期三中的忏悔和苦行也是必然。除以上两篇针对性论文,国内一些研究艾略特的专著虽亦对此诗有或多或少的涉及,但大多缺乏系统和详备的分析。本文笔者力图全面地对圣灰星期三加以注解,一来补充学界对此诗的认识和理解;二来有助于对艾略特整个诗歌创作重新理解,尤其是对其信仰转向后的文学创作的理解;三来透过艾略特创作中宗教的渗透理解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二、圣灰星期三相关宗教背景圣灰星期三作为宗教诗歌,必然和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艾略特本人已点明,圣灰星期三所表达的是“一个人寻找上帝的经历,以及以神圣的目标来向他自己解释倾述他自己强烈的人类情感”。 陈庆
8、勋著,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5页。为了试图证明圣灰星期三中作者这种“强烈的人类情感”的真挚,我们不得不先理清艾略特的宗教信仰历程。圣灰星期三中的宗教情怀首先是由诗人的宗教信仰历程所决定的。艾略特自小与宗教结缘,他出生于信仰唯一神教(Unitarism)教派的美国晚期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祖父威廉格林利夫艾略特是唯一神教的牧师。艾略特“视他为从地狱里管制着他的儿子和儿子的儿子们的人和一位墓碑上刻着公职戒律的莫西”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页。在正统的宗教观点来看,唯一神教不过是一种邪教,因它只相信有唯一的上
9、帝,不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教义,在信仰上可称为上帝一体论(monarchianism)。由于其不相信耶稣的神性,因此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基督徒。艾略特童年时期时另一个非常亲近的人保姆安妮邓肯对他今后的信仰有很大影响。安妮邓肯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经常与幼年的艾略特讨论上帝存在的证据,还经常带他去当地天主教堂。在艾略特关于亚瑟蒙斯的论文中,他回忆起幼年时敏感的自己被雕塑、腊片和熏香弄得精神恍惚。这种奇特的感觉可能加快了他日后改变信仰的进程。1906年6月底,艾略特考入了哈佛大学。据他堂哥说,此时他对唯一神教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然而,却仍有一股强烈的“使命感”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
10、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7页。在哈佛的求学生涯中,艾略特遇到一位对他影响极其深远的老师,被艾略特称为“亲爱的大师”的欧文巴比特。是巴比特最先把艾略特的兴趣引向了梵文与东方宗教。艾略特在哈佛的最后几年中热衷于佛教,据斯蒂芬斯彭德回忆他与艾略特的谈话,艾略特曾表示在写荒原时一度想改信佛教。研究生时,他也努力学习梵语和印度哲学,还学习了佛教课,后来他回忆,在这些学习中,他获得了些许“神秘的领悟”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5页。,走上了导师巴比特和保尔艾尔玛莫尔走过的哲学学派之路探讨东方宗教(尤其是非欧洲
11、宗教)的真谛,靠几乎完全不同于祖先的基督教的哲学来解决美国问题。从艾略特做研究生时研究神秘主义与佛教这点来看,他已经有了宗教感受,但还谈不上宗教信仰。当然他最终确实背离了自己家庭的宗教,放弃了祖父所信仰的唯一神教,拒不承认自己在那个基督教派中成长起来,尽管他是在祖父的弥赛亚教堂受洗。然而,像埃涅阿斯和他的家神一样,艾略特愈是背离,他背后的家庭愈彰显出无形的力量,以至于他把唯一神教斥之为苍白无力的异端邪说之后很久,仍在反复探讨这一信仰。而且他的确生来就被条理清晰的基督教所吸引:他在夜校讲座中已经提出“文学艺术中的古典主义者(他自命属于这一范畴)大多是要信奉天主教的” 转引自:(英)彼得阿克罗伊德
12、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28页。1919年,他曾研究过约翰多恩和朗斯洛安德鲁斯的布道,甚至认为它们是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并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甚至约翰多恩布道中的冥想为圣灰星期三提供了诸多图景。但当时,他基本还是持一种客观态度看待基督教。1921年,他论述伊丽莎白时代和詹姆士时代某些诗人智慧时,他认为这种智慧导致对宗教的理解且只有在对“宗教的理解”中才能完成。艾略特的朋友们也都十分了解他对宗教生活的同情态度。1924年他在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封信里说,牧师对他总有一种吸引力,他还可能去做礼拜。促成艾略特最终的宗教皈依的因素之一还有他的第一次婚姻。1915
13、年他遇到了薇薇安海格伍德,一个炽热、欢乐、有强烈自我意识、神经紧张几乎到了过敏程度的女孩。不久,两人便登记结婚,然而谁也没有事先通知双方父母。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一个草率的决定。艾略特后来曾论述过选择的可怕性有些决定如何不可挽回,如何会酿成一生的悲剧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50页。结婚以后,面对父亲的否定,母亲的失望和担心,以及本来来自父母的经济支持的断绝,艾略特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重新获得母亲的肯定。加之妻子日益神经质的脆弱以及身体状况愈发恶劣的问题,家庭负担的沉重,经济负担的繁重,艾略特无论工作、生活还是精神都遭受着严重的考验。年复
14、一年,婚姻逐渐变成了愈见恶化的痛苦的考验,艾略特本人亦已被折磨得疲倦不堪,有时会意识到自己“是在黑暗中跳舞”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53页。在此种境遇下,艾略特确实需要一种精神信仰来治愈精神上的痛苦,然后重获一个新的开始。 Joh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0.1922年,荒原的出版给艾略特带来了很大的声誉,同时亦掺杂着恶名和诋毁,艾略特开始经受一种精神历练,而这也将界定从此他作为人、作为作家的余生 Joh
15、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80.。艾略特的精神和信仰生活开始转变,虽然起初微妙,但的确清晰可见对基督教的投身 Joh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6.。他曾在一篇文章中表示希望向“身外的某种东西降服”,他无比迷恋于从伦敦的教堂中找到宁静,因为在那里“孤独的来访者”(显然还不是崇拜者)可以逃避尘世的喧嚣与污秽。安宁、平静和逃遁,这些是艾略特所认识的宗
16、教生活的主要特征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29页。1926年去罗马访问时,艾略特跪拜在米开朗琪罗的圣母怜子图前,这一举动使他的亲戚们感到吃惊。在改变信仰之前,他已经在圣公会接受定期培训,并参加晨礼拜了。在圣公会里,艾略特参加了英国天主教运动。1927年年初,艾略特向他的朋友,美国牧师威廉福斯司特德征求意见,请他帮助自己正式加入圣公会。但他要求对此绝对保密。此前,他已为自己铺好了路,在温德姆路易斯所创杂志敌人的1927年1月号刊上,他驳斥了伊阿瑞查兹的荒原致使“诗歌完全断绝了与所有信仰的联系”的观点,声称他从未构想将诗歌与他所称的信仰
17、相分离。他又在日晷杂志中声称人的主要特性是赞美上帝。1927年6月29日,艾略特完成培训后,被圣公会在科茨沃尔兹的芬斯托克教堂吸收入会。1928年,他终于向外界宣布了皈依宗教的消息,在新发表的为兰斯洛特安德鲁斯而作的评论序言中宣称自己是“文学上的古典派、政治上的保皇派和宗教上的英国天主教派。” 陈庆勋著,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对于他的大多数读者而言,这个意想不到的老旧的决定是如此唐突,以至于先前那些为他赢得“批判传统信仰、文学形式和语言的改革者”声誉的努力都付诸东流。同辈人中亦不乏质疑的声音。圣灰星期三在1930年发表后不出所料地收到混乱反响。甚至他的朋友刘
18、易斯认为这是“熟练的政治攀爬” Joh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毕竟在英国圣公会与经济、政治力量混乱地纠缠在一起,许多人认为曾经那个现代派诗人和不拘泥成规的艺术家灵魂变得软弱而服从于当权派,融入社会主流,而并非只是为了皈依于上帝 Joh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然而对于艾略特,圣公会与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以及与君主制的联系使他确信
19、,在这里,而且也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以上三方面在形式上的结合。艾略特所具备的英国人少有的传统意识以及渴望秩序的天性,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英国圣公会反对称颂都铎王朝政体光荣业绩不谋而合。艾略特关注于自我命运的同时更关注社会命运,他所担心的是社会无情向前奔走的同时世界变得彻底世俗主义、实利主义。在哈佛时对于人类学的学习已经使他认识到宗教作为一种原始的必需力量对于整个社会的社会文化重要性 Joh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他所追求的文明社会中人类的最高目标是“把最深刻的
20、怀疑主义与最深厚的信仰联接起来。” Joh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他意识到了存在于一切人类事物之中的所谓“空虚”的东西混乱、无意义、徒劳 (英)彼得阿克罗伊德著,艾略特传,刘长缨、张筱强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51页。,只有依靠宽宏的信仰才能对之加以理解和忍受。自祖父所遗传下的对于“原则”的天性追求,使得艾略特努力去发现一种超凡的信仰,并通过它使人类可能经历丰富而必需的共同的生命经历,并自此人类之间真正的亲密关系得到心灵和情感上的保证 John
21、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26.。换言之,艾略特努力发现最能使人信服的信仰,并逐步理解和接受它。恰好,基督教信仰中为一个深深意识到原罪的灵魂所作的祷告与忏悔,以及慰藉与赦罪,深深地撼动了艾略特。据斯蒂芬斯彭德回忆,艾略特曾在与弗吉尼亚伍尔夫的谈话中试图传达祷告的重要意义,它使精神和感情完全集中在一个外在力量或存在之上,以致全神贯注到被融入这个存在之中。正如VA德曼特所言:“在宗教、甚至可能在皈依宗教一事上,他感到身不由己,是已经被选择好了的,而不是去选择。”而这种所谓的“被
22、选择”并非是趋利的世俗选择,而是他在追求“原则”的天性驱动下的诚意的对于信仰的选择。这样的宗教信仰日渐鲜明地反映在他的作品中。自1925年始,艾略特开始在一系列诗歌创作中探索皈依的可能。他所考虑的宗教主题无疑暴露于阿丽尔诗中,这也是他自学生时代以来第一次明显的宗教意味的尝试。类似戏剧独角戏的阿丽尔诗提供了一系列艾略特关于宗教和自身精神、信仰追求的思考,虽然很难说它们是否真正是对于基督教信仰的真诚追求,也或许这只是进一步探索一种不同寻常的“声音”、一种表象人格,或是一种无关承诺和献身的信念。然而,当公众终于得知艾略特加入圣公会,任何对于他的宗教信仰的质疑不论是否消失,已变得不那么重要。他已做出了
23、自己的决定并力图将此高尚的信仰进行到底。恰恰是阿丽尔诗记录下了这封寄给永恒信仰和坚持的信的地址,而圣灰星期三为这封崇敬之信封上了信封 Joh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26.。圣灰星期三作为六首小诗组成的诗组发表于1930年,在此之前已有三首诗以不同诗名事先发表,其中:第二首小诗致意(“Salutation”)发表于1927年,第一首小诗因为我不再希望(“Because I do not hope”,又名“Perchio non spero”)发表于1928年,第三首小
24、诗楼梯的至高点(“Summit of the Stairway”,又名“Som de lEscalina”)发表于1929年。其他三首亦分别命名为:“Jaw Sea Io Jorn”、“身着火焰般色彩的衣装”以及“您的意愿”。六首小诗看似无太多相关,实则组成有机统一体。在新的安排架构下,全诗建构出一套合理结构展现了诗人关于“大斋期”(Lent)的精神体验。今日所说的“大斋期”是基督教的教会年历中一段重要的节期。通过大斋期,其一纪念摩西战胜法老渡过红海、以及耶稣战胜撒旦;其二教会希冀自身每年达到更新、净化;其三信徒们通过禁食祷告、悔罪,以诚实的心灵去亲近上帝,纪念耶稣基督为他们所成就的救恩,体会
25、他的温柔、爱、勇敢、孤寂与牺牲,同时达到自身的洗刷、净化、治愈、回归,预备自己迎接复活节,使自己的属灵生命得以更新和强化。大斋期自“圣灰星期三”(Ash Wednesday)开始。“Ash”即指“蒙灰”,因基督为人们所受的苦,信徒以痛悔的心认罪祷告。在传统教会举行的灰日崇拜上,牧师带领大家在教会门口焚烧木十字架(或使用去年棕枝主日所留下来的棕枝),侍火熄灭后取其灰,在崇拜认罪祷告中,信徒列队走到台前,认罪并由牧师在他额上以灰画上十架记号,仿效旧约时代的人表达哀伤和悼念。三、圣灰星期三解注圣灰星期三英文原版共219行,裘小龙版译本共216行。 文中所引圣灰星期三中文译文皆出自:(英)T. S.艾
26、略特著,四个四重奏灰星期三,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英文原版、裘小龙译本、笔者译本,皆详见附录。每一首小诗都与教会所提供的教徒通过庄严的祈祷和补赎以达精神历练相关的传统宗教仪式紧密联系,表现了灵魂在神秘的仪式和探寻中历练,“行走于”耶稣受难日的“黑暗”,努力摒弃、历练、经验,最终站在耶稣复活的“白光”之中,企图实现斋戒期至高之目标。整个诗歌结构看似象征着灵魂的忏悔以达复活节时精神的胜利。大斋期中六个星期对自我生的历练、悔罪、革新展现在诗中形成六个部分超脱,告诫,苦行,补赎,放弃,仁爱。“整个诗组诚然闪烁着宗教和传统文学色彩,然而它最独到之处还是它自身。” Helen Gardner,
27、 The Art of T. S. Eliot, London: the Crescent Press, 1949, p.99. 自艾略特的诗学论文中,我们能发现艾略特已经提供了一种解读圣灰星期三的方式即讲其视为一种“冥想”。此诗也很明显是他的“诗的三个声音”的理论实践之一。艾略特这样区分“诗的三种声音”:“第一种声音是诗人对自己说话的声音或者是不对任何人说话时的声音。第二种是诗人对听众不论是多是少讲话时的声音。第三种是当诗人试图创造一个用韵文说话的戏剧人物时诗人自己的声音;这时他说的不是他本人会说的,而是他在两个虚构人物可能的对话限度内讲的话。” 王恩衷编译,樊心民校,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
28、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49页。他进一步解释道:“关于第一种声音的诗主要并不是同任何人交流的诗这种类型的诗并不一定就是我们笼统地叫做抒情诗的东西。” 王恩衷编译,樊心民校,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56页。他认为“和我的第一种声音相关联的是直接表达诗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意义上的抒情诗。” 王恩衷编译,樊心民校,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57页。他更倾向于称之为“冥想的散文” 王恩衷编译,樊心民校,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57页。圣灰星期三无疑偏向于诗人所言的“第一种声音”,诗中灵魂的朝圣之旅也表现了诗人情感乃至灵魂的历
29、练。1.“因为我不再希望”圣灰星期三开篇第一首“因为我不再希望”奠定了全诗冥想深思的基调,记录了精神的苦行和转变。诗中的“我”向上帝祷告祈求神的怜悯,力图摒弃俗世中种种幻象的希望,希冀在上帝的恩赐下洗净身心,不再堕落与俗世的时间王国之中。开篇三句“因为我不再希望”(1-3)来自于中世纪意大利诗人圭多卡卡瓦尔康蒂(Guido Cavalcanti)的诗篇因为我不再希望(“Per chio no spero”,又“Because I Do Not Hope”),艾略特只是将“因为我希望再不转身”(“Perchio non spero di tornar giamai”)句中的 “转身”一次由“re
30、turn”改为“turn”。卡瓦尔康蒂的诗作于流放萨兰闸之时,艾略特同感于卡瓦尔康蒂身为“流放之人”而被拒于天国之外,祈求上帝的仁慈。放弃(renunciation)俗世的思想透过此三句清晰传达出来。“我”宣布放弃所爱所念,甚至做好了“死亡”的准备。这种遗失之感随即调转成为一个更宽阔范围内的尘世失落和放弃的主题,“我不再努力为得到这些东西努力”(5)一句通过援引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第二十九首中的“希求这人的渊博,那人的内行”句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梁宗岱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得以表达,表明了“我”意识到“世俗”是灵魂趋于平静的障碍。诗人突出强调现
31、世的力量皆为短暂,如此幻灭的“我”对于人间社会的某种失望。“我”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失败和无能,无法将自己的目标超越个人夙愿,从而面临诸多精神困境。“我”努力否认之前关于各种幻象和欲望,即关于“这些东西”(5)的种种思虑妒忌、骄傲、漠然等诸种情绪。而这种失望多少更倾向于因某种顺从而不得不产生的“醒悟”,试图下决心不再回首人间。可见此时诗歌的基调明显是毫无挑剔的谦逊、顺从。然而第一节最后三句语气陡然变化,在反诘的句式中,谦卑转为某种蔑视和挑战,与其变得多少有些刺耳“我”质疑“年迈的鹰”(6)和“寻常的王国”(8)。爱伦塔特曾将艾略特早期诗歌、特别是荒原中典型的讽刺(irony)语调与圣灰星期三中的
32、谦卑(humility)精神做了比较,讨论了谦卑和讽刺在精神上的一致:“谦卑是一种主观的精神品质的特性:它是如此的普遍、无形,只能暗示而不可见。讽刺则是可见的、特别的,且是谦卑的客观情况。讽刺是一事件或处境的客观特性,刺激着我们谦卑的能力。” Allen Tate, Reactionary Essays on Poetry and Idea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k, 1968, p.216.他还详细地解释了“谦卑”和“讽刺”在审美上的不同,他注意到:“圣灰星期三中足够意味深长的单一讽刺的段落便是第一首诗中的第一节。此段落客观代表了诗人目前对自身的
33、所思所想,建立起他对于自身价值的谦卑,这也决定了诗歌后来的方式。” Allen Tate, Reactionary Essays on Poetry and Idea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k, 1968, p.217.“年迈的鹰”(6)是对诗中的“我”的暗讽。中世纪基督教传说鹰到了老年能在阳光和泉水中重新恢复青春, (英)T. S.艾略特著,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因此该意象也表达了“我”渴望皈依上帝从而在上帝所赐的荣光中获得精神上的新生。通过对于现世王朝的反问、对于在世俗中的“我”亦或所谓的“年迈的鹰”的讽刺,
34、诗人试图传达一种放弃的胜利。这种放弃并非单纯源由于对世俗生活的厌倦而顺从,而是真正的主体所做的积极的决定。而此时我们再回看前三行,即可发现它们字里行间中更多了一份主观肯定和积极的成分。所谓的“顺从”进而推至成为一种个人意志。然而,“我”对于“放弃”的确信却又在第二节中崩塌,通过支离破碎的表达,可见“我”的处境似乎进一步恶化。诗人竭力在力图“证明”,却缺少了先前坚定地“断言”。“我”意识到“确凿的时刻”(10)的“光芒”(10)虽然真实,却终将是“摇晃的”(10),“寻常的王朝”(8)的“唯一名副其实地转瞬即逝的力量”(13)也是一种虚假的力量,虽然现世的成就承诺着某种看似永久的和平。认识到这点
35、,“我”开始祈祷着能够去除这种幻念,虽然这种行为可能会伴随着疼痛和艰难。面对这种“转瞬即逝”(13),“我”的内心境遇无比荒芜。“我”领悟到在现象世界中行走,在“群树生花,小溪流淌”(15)中行走,即在“无所存”(15)的王国中行走。“群树生花,小溪流淌”描绘出某种愉悦感官的幻觉,然而这里也正是“我”的流放地。“无所存”(15)一词,多少透着单纯和天真,却也表明了朝向上帝的境界的艰难“一无所有”。但这似乎又和“我”所向往的美好的境界自相矛盾,因此“我”在追求与彷徨中始终是焦躁不安的。因此,“我”的生命始终在“不平静旋转”(155),焦躁地围绕这并不居中的、所谓的“居中”旋转,“抵抗那道”(15
36、5)。如此,“无所存”(15)代表着一切的虚无、苦行、缺席、流放、黑暗,乃至类似地狱的审判。“再”(15)字也可见在此之间“我”曾在较低境界的宇宙界中寻找过自己那难以超脱个人夙愿的目标,但找到的却永远都是“无所存”(15)。“再”(15)字在第一首诗的英文原版中共出现六次:“因为我不再希望重新转身”(1);“那里,那里群树生花,小溪流淌,因为再无所存”(15);“因为我不能希望重新转身”(23);“因为我不再希望重新转身”(30);“因为那已经做的,不会重新再做一遍”(32);“虽然我再不希望重新转身”(184)“再”将上下文中看似没太多联系的部分联系在了一起。更重要的是,它将所有“转瞬即逝”
37、(13)的、“消失了”(8)的部分和“这些东西”(5)、“无所存”(15)联系在一起。可见“我”的某种不可名状的焦虑,荒芜的处境也变得更加岌岌可危,桎梏于徒然的盘旋,在幻觉中不得超越。焦虑之下,“我”却恰恰因此而开始认识了所谓的“虚无”(nothingness)王国:诗文中不断重复着“时间”(16)和“地点”(17)这样的关键词。诗人在“虚无”王国中意识到,俗世的“时间王国”必要遗弃于身后,因为“时间永远是时间”(16),而“我”所要追寻的“真知”恰恰为其所限,因为它始终只在时间中的某一刻才真实,但它桎梏着“真实”。“我”因对“虚无王国”有所认知而欣喜,然而这种认知远远不够,因为在其外亦存在其
38、他的诱惑,如“那张受了祝福的脸”(21)和“那个声音”(22)。“我”采取的是“拒不承认”(21)的态度。“拒不承认”(21)暗示了忏悔者决意改变。“我”要放弃的,除了第一节中那充满野心的努力和第二节中“群树生花,小溪流淌”(15)的诱惑,还有“那张受了祝福的脸”(21)和“那个声音”(22)它们亦属于“这些东西”(5)的一部分。所有这些暗喻都象征着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s)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饕餮(暴食)及色欲。“我”因意识到这些幻想并决定放弃而“欢欣”(24)。“欢欣”在第三节中出现了三次,“我”“欢欣”因认识到了一切皆为尘土且归为尘土,反对那些朝向诸种幻想的无
39、价值的“转身”。这样一种认知使“我”欢欣着“我”将放弃的俗世和尘埃。“欢欣”出自圣经诗篇的求主垂怜(Miserere),“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PSALMS 51:8)旧约诗篇51:8,出自:中国基督教协会,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圣经中文和合本,2009年,第900页。(后文中所引圣经原文皆出于此,因此有所省略)。“于是我欢欣”(24)是对弥撒仪式的认罪祷告的一种回应。 第四节中“我”开始向上帝祷告,其中主语“我”变成“我们”,可见“我”与朝向上帝的众信徒相联系,形式如圣经诗篇或其他礼拜仪式中常常出现的那样,诗人此时似乎初步明白了自我努力的方式:若以
40、“我”为中心则达不到更高层次。所以为了达到更高的国度,诗人必须要“忘却/那些我与自己讨论得太多/解释得太多的事情”(27-29)。在“更为渺小和干燥的空气”(36)中,“年迈的鹰”(6)已不能再飞翔,“翅膀”(34)“仅仅是拍击空气”(35),“我”的意志也变得“渺小和干燥”(36)。因此“我”才祈祷“祈愿对我们的判决别太沉重”(33)。此时,全诗终于出现了一个句点“叫我们坐定。”(39)说明这个祷告到此结束了。“我”向上帝祈求“操心或不操心”(38)的能力,为了不至于对周遭漠不关心,“我”必须学会“操心”。为了避免“转身”错误,“我”又必须要学会“不操心”。而自此至彼的超越,即在于“我”祈求
41、的“教我们坐定”的能力。这个能力,将带领“我”进入“这个寂静的道的重心”(157)。最后“现在为我们这些罪人祷告,在临终时为我们祷告”(40)一句来自罗马天主教祷告中的原话。在第一首诗中,艾略特描绘了灵魂成长之初所面临的问题,诸多问题也和他在阿丽尓诗中所提及的内容形成互文:“日复一日,越发迷惑、冒犯,/周复一周,越发冒犯、迷惑;/因为那种是和似乎是的规则,/还有可能和不可能,欲望和抑制,/生存的痛苦和梦的麻醉/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后面的/窗台上蜷起了小小的灵魂。” (英)T. S.艾略特著,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30页。艾略特实际表达了另外一种死亡的形式,他阐明的是某
42、种精神的死亡,如干燥的萨尔维吉斯中所言的幻象的终结:“而死亡的时间又是在每一个时刻。” (英)T. S.艾略特著,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210页。这死亡,亦即新生。 2.“致意”如果说第一首诗所呈现的图景是一个力图转身、摒弃世俗、却又不得不徘徊、于是虔诚祷告上帝祈求神赐的主人公形象,那第二首诗则继而呈现了一个“精神的新生”(spiritual rebirth) Devid Moody ed., T.S. Elio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2000, p.136.。第二首诗行文中动词的时态已不同于第一部分的“现在时”,而是“
43、过去时”和“现在时”交错混杂运用。时态的神秘不定,证明了灵魂生命的神秘不定,恰恰又展现了灵魂的统一体。虽然“时间永远是时间”(16),但时间却又仅仅只是时间,而灵魂终将趋向不朽,这终将与时间无关,更无关于时态。此外,第二首诗中隐含着一片荒原,在这片荒野中,旷野教父(Desert Fathers)寻求生命和灵魂,希伯来人得以洗礼和新生,基督(Christ,the New Adam)抵抗住了亚当(First Adam)所没有抵挡住的撒旦的诱惑荒野暗喻着大斋戒的净化灵魂和精神就此新生。开篇描绘了一副桧树下豹子饱餐一顿的图景。“桧树”(42)不禁让人联想到格林童话中桧树的故事,它在故事中象征着新生命的
44、美好开始。此处“桧树”的意象也同样暗示着圣经旧约列王纪上中以利亚的故事。以利亚为了逃避耶洗别的追杀,在旷野中走了一日的路程来到一棵桧树下,求耶和华取他性命,而天使却给他带来了食物,并唤醒了他,指引他继续前行,四十个昼夜后他终于登上何烈山,找到了耶和华(1 Kings 19) 旧约列王纪上19,第567页。“桧树”是以利亚生命中重要的庇护,暗示着其后生命灵魂终究得到归宿。诗中的“桧树”也同样暗示此意,灵魂终将找到归宿。而“白昼的阴凉”(43)谈及了“人类的堕落”(the Fall)上帝与亚当和夏娃的冲突:“天气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
45、的面。”(GENESIS 3:8) 旧约创世纪3:8,第4页。上帝得知他们偷食了生命树的果实,审判了他们,而在此后却亦给予他们不绝的爱、关怀和承诺。这幅图景中的主角“豹子”(42),乃意味着“精神的新生”。当然,这并非一个全新的自我,而是一个已消解的自我。“我”的躯体被“三只白色的豹子”(42)狼吞虎咽地吃光。“白色”这个形容词毫无疑问展现了一种纯洁的观感,宛如洗礼时那白色的洗礼服般神圣而纯粹。神曲地狱篇中但丁也遇到的三个猛兽:彩色的豹“刚走到山势陡峭的地方,只见一只身子轻巧而且非常灵便的豹在那里,身上的毛皮布满五色斑斓的花纹。它不从我面前走开,却极力挡住我的去路,迫使我一再转身想退回来。”;
46、狮子“但这并不足以使我对于一只狮子的凶猛形象出现在面前心里不觉得害怕。之间它高昂着头,饿得发疯的样子,似乎要向我扑来,好象空气都为之颤抖。”;母狼“还有一只母狼,瘦得仿佛满载着一切贪欲,它已经迫使很多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它的凶相引起的恐怖使得我心情异常沉重,以致丧生了登上山顶的希望。”与圣灰星期三中的“三只白色的豹子”不同的是,但丁笔下的猛兽并不代表“净化”的意味,而分别寓言式得象征着淫欲(Incontinence)、骄傲(Pride)和贪婪(Greed) (意)但丁著,神曲地狱篇,田德望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1-2页。它们三个都非常饥饿,而诗人面对他们时亦充满恐惧。但艾略特笔下的豹
47、子虽“饱厌”,却非暴食。“豹子”据圣经记载是上帝执行摧毁使命的使者。正如但丁初见贝亚特丽齐时曾产生的那三种“精灵”“说真的,在那一瞬间,潜藏在我内心深处的生命的精灵开始激烈地震颤,连身上最小的脉管也可怕地悸动起来,此时,居于高出(所有感觉的精灵都在这里面传递感知的功能)的充满活力的精灵开始大为惊异,它特别对视觉的精灵说话在那一时刻,住在摄取饮食部位的自然精灵开始哭泣” (意)但丁著,新生,钱鸿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2页。被器官肝脏(liver)所消化,圣灰星期三中诗人的罪行被代表了苦行消解的原动力、罪恶的惩罚者“三只白色的豹子”所消解。但它们所吞食的不过是诗人有罪过的幻象,而留下
48、的是诗人身体和灵魂名副其实的部分。在三只豹子的吞噬下,“我”的骨头被“重新得到”(55),变得干净而纯白,也为“我”的灵魂生命重新开始奠定了基础。“我”的身体被新的血肉覆盖,从而获得了新的力量来源。骨头若无血肉覆盖是不完整的,而它们的重新修复则是类似于“一般复活”(General Resurrection)。“我”在朝向上帝的第一步赎罪中的诸种罪恶的意志和罪行被豹子们消除。骨头被消解后,上帝发问:“这些骨头是否会活下去?”(47)圣经以西结书中,耶和华问道:“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EZEKIEL 37:3) 旧约以西结书37:3,第1392页。艾略特仅将句中“能”的“can”改为“sh
49、all”,保留了反诘的语气。这些骨头“圆圆的空洞”(45)虽是空的,但它不同于第一首诗中所说的空无一物。如圣经所言,主耶和华“必将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活了。” (EZEKIEL 37:5) 旧约以西结书37:5,第1392页。这种复活是通过神把人从死地提升,使他们能在他的面光之中得着全新又永不完结的生命。而骨头在摒弃俗世和洗涤罪行中是“伪装的”(52),乃至“四散的”(89),它们甚至掩饰了某种转身的潜能和许诺。这“伪装着的我”(52)渴望“遗忘”(59),也渴望“被人遗忘”(60),“我”将事迹献给“遗忘”(
50、forget),将爱情“献给沙漠的后裔和葫芦的果实”(54)。死亡是荒漠的子孙,葫芦的种子是有毒的。葫芦在久旱的荒漠上生发繁荣,荒漠上成长起生命,却又是死亡。因此,诗人的爱情终将死亡,却又似生发、存在。“葫芦”指向的是圣经约拿书中约拿所在的棚阴上的葫芦。神因尼尼微人畜披上麻布禁食禁饮地告赎而宽恕他们,约拿先知为此而发怒,生气地出城坐在城东边自己搭的棚中,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耶和华于是安排一棵葫芦为其遮阴,次日又致其枯槁,以此教育约拿爱惜子民(Jonah 4)。 旧约约拿书4,第1487页。 此时,“夫人”再次出现,身穿“白色的长袍”(58)。“白色”无疑象征一种纯洁,此外,它同样也暗示着某种“
51、存在”,也暗示着某种“缺席”。如燃烧的诺顿(Burnt Norton)中所写:“一道白色的光,静止而又运动,/歌颂而无动机,集中而无/消失” (英)T. S.艾略特著,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86页。,“白色”是玛丽的颜色之一,所有的颜色都存在于白色中,却又似乎全不存在。它似乎包罗万象,却又似纯洁无比。正因为它的“汇聚”、“集中”,“骨头的雪白”(59)才能“虔诚不已、目的专注”(62),才有能力复新、完成。“我”于是终于准备好,接受上帝的指挥,像上帝指挥以西结那样:“耶和华的灵降在”(EZEKIEL 37:1) 旧约以西结书37:1,第1391页。他身上,“向风发预
52、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EZEKIEL 37:9) 旧约以西结书37:9,第1392页。,于是生命的枯骨注定复活。在上帝的命令下,“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EZEKIEL 37:11) 旧约以西结书37:11,第1392页。,上帝“使他们从坟墓中出来”(EZEKIEL 37:12) 旧约以西结书37:12,第1392页。尽管他们的“指望失去了”(EZEKIEL 37:11) 旧约以西结书37:11,第1392页。,他们仍将统一,并回到自己的国度去。这里的“风”暗喻着圣灵显灵。在圣经约翰福音中记载的耶稣与尼哥底母谈重生,耶稣说:“风随着
53、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JOHN 3:8) 新约约翰福音3:8,第161页。在圣经使徒行传中五旬节时圣灵降临也是以风的形式,“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来,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ACTS 2:2) 新约使徒行传2:2,第203页。“风”不仅标志着圣灵的降临,也是人类生命的开始。如圣经创世纪所言,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GENESIS 2:7) 旧约创世纪2:7,第3页。因此,上帝对人的命令通过风,“给风的寓言,只给风,因为只有/风会倾听”(63)。风的预言之下,“骨头叽
54、叽喳喳地负着/还有蚱蜢的负担”(64-65)。“蚱蜢的负担”来源于圣经传道书中的“杏树开花,蚱蜢成为负担”(ECCLESIASTES 12:5) 旧约传道书12:5,第1069页。,“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ECCLESIASTES 12:8) 旧约传道书12:8,第1070页。伴着虚空和死亡,骨头“叽叽喳喳”地回应上帝对大地的致词。这种“叽叽喳喳”(chirping)不同于莎士比亚笔下“像云雀破晓从阴霾的大地/振翮上升,高唱着圣歌在天门” (英)威廉莎士比亚著,莎士比亚全集(第八卷),梁宗岱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页。,也完全不同于第一首诗中的“悲伤”,而是可爱的颂歌,
55、歌声中透着无尽欢愉。它们的确该欢愉,为这幻象终于为正确的爱所取代。骨头的“负担”(burden)亦即一种爱。是爱(love),而非欲(desire),正如在燃烧的诺顿中艾略特试图区别的:愿望本来就是运动,愿望的本身并不值得愿望;爱的本身并不惹人爱;只是运动的原因和终结,没有时间、没有欲望,除了在时间的这一点外,陷于形式的局限之中。 (英)T. S.艾略特著,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191页。“爱”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是寂静的,是世界旋转中确定的重心。“爱”完全体现在“夫人”身上。骨头和蚱蜢唱的是模仿罗马天主教对圣玛利亚的连祷词。圣歌中歌颂的首先是“夫人”,然后是“花园”或
56、耶和华 神。对于“寂静的夫人”中的“夫人”,有诸种解释:其一,她可能暗示的是以色列教堂雏形。“统一于/沙漠的静谧中。”(92-93)的骨头,象征着圣经以西结书中上帝诺言的实现,“我的民呐,我避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EZEKIEL 37:12) 旧约以西结书37:12,第1393页。“我的仆人大卫比作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EZEKIEL 37:24) 旧约以西结书37:12,第1394页。在希望和仁善的引领下,骨头“四散闪光”(87),因信仰和天赐宽恕而净化。虽然它们仍只能“嘁嘁喳喳”(64)对于“寂静的夫人”(66)的赞美和感谢。他们赞美童女玛利亚
57、宛如花园中的玫瑰。其二,这首圣歌也是对于但丁的致意,它将神曲天堂篇的最后三章和罗马天主教对玛利亚赞美的圣歌融为一体。“夫人”可能是一个贝亚特丽齐式的人物,“一个修女,或者甚至是一个童女(Virgin),或者她也可能仅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但是她是被展示出来的,通过祈祷的严肃语调,展现在宗教图景的礼仪中。” Allen Tate, Reactionary Essays on Poetry and Idea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k, 1968, p.219-220.“夫人”是“安宁的”(67),因其谦卑以及无条件服从上帝的意志,同时她又是“苦恼的”(67
58、)。她被“时间”和“永恒”交叉撕扯,被圣经路加福音中西面的寓言撕碎:“这孩子被立,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作诽谤的话柄,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LUKE 2:34,35) 新约路加福音2:34,35,第100页。她又是“完整的”(68),是一切之源。她的童贞暗喻着全部,她孕育了万生(All),因此拥有处女的完整。只有她才真正知道如何“焦虑而恬静”(72)地坐定,如何关心或不关心,知道如何抵制讽刺的顺从。她因成为上帝的侍女而“精疲力竭”(71),亦因此而“生机洋溢”(71),个人私欲的终结恰恰预示着永恒灵魂的发端。她才真正能忘记诗人想忘记的,才能
59、真正为众生所忘记。因此她是“遗忘的玫瑰”(70),亦是“记忆的玫瑰”(69),是盛开在干骨上的百合花。基于如此精神上的完成,“唯一的玫瑰”(73)变成了“现在的花园”(74)。骨头歌唱着“光荣归于圣母”(86),“寂静的夫人”诞生万物,耶和华神创造一切善行善事,因此“在那花园/爱情结束一切。”(74-75)然而这结束,恰恰意味着新的开始。爱情止于花园,亦止于苦行的“我”:曾经的愉悦肉感的低层次的爱得以净化和升华,甚至完成。在时间的限度内,“没有满足的爱情的/最终的折磨”(77)终于得以“满足”,“没有尽头的不停的旅程”(81)终于“尽头”,“无法结论的”(83)结论也许就此“结论”,“没有词的
60、语言以及/不是语言的词”(84-85)也许就此表达。圣奥古斯丁所警告的那些坐立不安的灵魂终将安定,直至他们余生荣归于圣母玛利亚,荣归于耶和华神。而真正的爱也终将在花园中得以欢愉。但这个花园并非人类万民重获的天堂,亦不是尘世的天堂,更不是爱情的花园,虽然艾略特竭尽描写希望把它推于那个高度,但它始终是一个或高或低的游离之处。在花园之后,也许是伊甸园,我们的意志最接近也最疏远上帝的地方。在苦难的花园中基督为主准备好了自己的意志为人类万民受难,也因此在花园中他被埋葬,继而复活。这也许是一个重生的花园。它是终结,却恰恰是起点。唱着圣歌的骨头在“桧树”下,在“白昼的阴凉”中,亚当和夏娃离开伊甸园开始了流放
61、,而被吞噬的骨头作为新的生命却开始真正“忘却他们自己和对方,统一于/沙漠的静谧中”(92),骨头超越了“划分和统一”(94)而找到了“我们的遗产”(95)。“我们的遗产”象征着圣经以西结书中上帝许诺于以色列的地界,“这地必归你们为业”。(EZEKIEL 47:14) 旧约以西结书47:14,第1411页。“他们必永得为业,/世世代代住在其间。”(ISAIAH 34:17) 旧约以赛亚书34:17,第1139页。,为此,“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ISAIAH 35:1,2) 旧约以赛亚书35:1,2,第1139-1140页。
62、3“楼梯的顶端”无论从语言还是意象上看,圣灰星期三的第三首诗表现的都是忏悔者在奔向上帝的良知历练和悔罪过程中诗人的一种痛苦的情绪。诗人试图向我们描绘的是灵魂努力攀爬出罪恶的黑暗、奔向“楼梯的顶端”(the summit of the stairway)的光明与和平。“楼梯”的意象诸多学者都做过猜测和评论,它象征的也许是通向圣十字约翰的神秘上升之路;也许是神曲炼狱篇中的飞檐;还可能是通往“圣彼得之门”(Peters Gate)的三步台阶;也可能是罗马教会中通向圣祭礼(Eucharist)的圣坛的三步台阶。普遍意见认为艾略特的“楼梯”意象主要是对但丁和圣十字约翰(St. John of the C
63、ross)的借用。楼梯成为某种净化的典范,它们不像是现时的真实,而更像过去时,炼狱式的记忆。它们揭示了一个神秘的改变过程。而走过这个台阶,“我们有过经验,但抓住意义,/面对意义的探索恢复了经验”。 (英)T. S.艾略特著,四个四重奏,裘小龙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第207页。根据安德鲁斯在1619年圣灰星期三的布道论悔悟,世间万物都“知道它们的季节”,按时回归,循此规律,人亦应知晓何时当该转向上帝。这种作为悔悟的转向本身即一种循环,包括两个转向点,其一是悔悟者全心全意转向上帝,其二是转身之后审视罪孽。轮在飞转,若不在这两个转向点转身,轮就会压倒悔悟者。 陈庆勋著,艾略特诗歌隐喻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16页。法语中有句谚语:“楼梯上的灵光”(Esprit dEscalierscalier)意思是说你找到答案的那一刻,却为时已晚。艾略特在圣灰星期三中将这“楼梯上的灵光”替换为“魔鬼一般的楼梯”(100)。“在第二节楼梯的第一个弯子上”“我”向后看,发现“恶魔”与“同一个形状扭曲”(98)搏斗着,而这个搏斗的身影恰恰是“曾经的自己” John Xiros Cooper, T. S. Eliot, Cam
- 温馨提示:
1: 本站所有资源如无特殊说明,都需要本地电脑安装OFFICE2007和PDF阅读器。图纸软件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压缩文件请下载最新的WinRAR软件解压。
2: 本站的文档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图纸等,如果需要附件,请联系上传者。文件的所有权益归上传用户所有。
3.本站RAR压缩包中若带图纸,网页内容里面会有图纸预览,若没有图纸预览就没有图纸。
4. 未经权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将文件中的内容挪作商业或盈利用途。
5. 装配图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保护处理,对用户上传分享的文档内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编辑,并不能对任何下载内容负责。
6. 下载文件中如有侵权或不适当内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立即纠正。
7. 本站不保证下载资源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时也不承担用户因使用这些下载资源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