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比较法视野下的法院附属调解制度研究
比较法视野下的法院附属调解制度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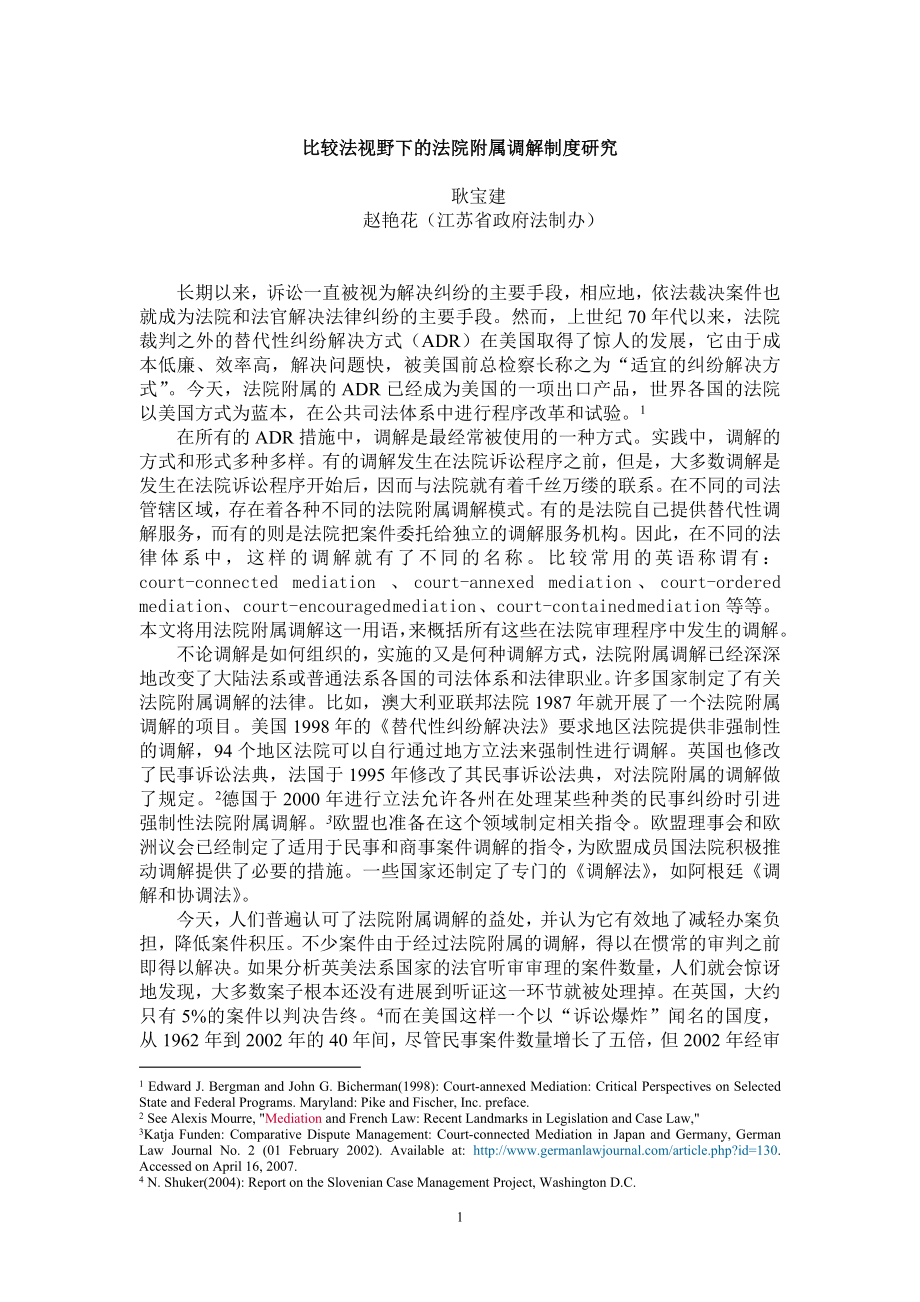


《比较法视野下的法院附属调解制度研究》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比较法视野下的法院附属调解制度研究(11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比较法视野下的法院附属调解制度研究耿宝建 赵艳花(江苏省政府法制办)长期以来,诉讼一直被视为解决纠纷的主要手段,相应地,依法裁决案件也就成为法院和法官解决法律纠纷的主要手段。然而,上世纪70年代以来,法院裁判之外的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在美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它由于成本低廉、效率高,解决问题快,被美国前总检察长称之为“适宜的纠纷解决方式”。今天,法院附属的ADR已经成为美国的一项出口产品,世界各国的法院以美国方式为蓝本,在公共司法体系中进行程序改革和试验。 Edward J. Bergman and John G. Bicherman(1998): Court-annexed Media
2、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elected State and Federal Programs. Maryland: Pike and Fischer, Inc. preface.在所有的ADR措施中,调解是最经常被使用的一种方式。实践中,调解的方式和形式多种多样。有的调解发生在法院诉讼程序之前,但是,大多数调解是发生在法院诉讼程序开始后,因而与法院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法院附属调解模式。有的是法院自己提供替代性调解服务,而有的则是法院把案件委托给独立的调解服务机构。因此,在不同的法律体系中,这样的调解就有了不同的名称
3、。比较常用的英语称谓有:court-connected mediation 、court-annexed mediation、court-ordered mediation、 court-encouraged mediation 、court-contained mediation等等。本文将用法院附属调解这一用语,来概括所有这些在法院审理程序中发生的调解。不论调解是如何组织的,实施的又是何种调解方式,法院附属调解已经深深地改变了大陆法系或普通法系各国的司法体系和法律职业。许多国家制定了有关法院附属调解的法律。比如,澳大利亚联邦法院1987年就开展了一个法院附属调解的项目。美国1998年的替代
4、性纠纷解决法要求地区法院提供非强制性的调解,94个地区法院可以自行通过地方立法来强制性进行调解。英国也修改了民事诉讼法典,法国于1995年修改了其民事诉讼法典,对法院附属的调解做了规定。 See Alexis Mourre, Mediation and French Law: Recent Landmarks in Legislation and Case Law,德国于2000年进行立法允许各州在处理某些种类的民事纠纷时引进强制性法院附属调解。Katja Funden: Comparative Dispute Management: Court-connected Mediation in
5、Japan and Germany, German Law Journal No. 2 (01 February 2002). Available at: Accessed on April 16, 2007.欧盟也准备在这个领域制定相关指令。欧盟理事会和欧洲议会已经制定了适用于民事和商事案件调解的指令,为欧盟成员国法院积极推动调解提供了必要的措施。一些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调解法,如阿根廷调解和协调法。今天,人们普遍认可了法院附属调解的益处,并认为它有效地了减轻办案负担,降低案件积压。不少案件由于经过法院附属的调解,得以在惯常的审判之前即得以解决。如果分析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听审审理的案件数量,人
6、们就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案子根本还没有进展到听证这一环节就被处理掉。在英国,大约只有5%的案件以判决告终。 N. Shuker(2004): Report on the Slovenian Case Management Project, Washington D.C.而在美国这样一个以“诉讼爆炸”闻名的国度,从1962年到2002年的40年间,尽管民事案件数量增长了五倍,但2002年经审判的案件数量却比1962年少了20%多,2002年经审判处理的案件只占全部案件数量的1.8%。 Marc Galanter (2004), The Vanishing Trial: An Examinatio
7、n of Trials and Related Matters in Federal and State Courts, JOURNAL OF EMPIRICAL LEGAL STUDIES, VOL. 1, No. 3, pp2本文试图通过比较不同法域的法院附属调解制度,总结附属调解的不同模式,并分析影响调解成败的原因,并针对中国的实践,提出几点启示一、法院附属调解与审判之间的关系:从对立到共生传统观点认为,审判作为一个对抗性的程序,法官一般作为中立者进行断案,并不去调合当事人间的分歧或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之争。法官坐在高高的法台上,双方当事人提出他们的证据,对案件事实以及适用法律进行口头的对
8、抗性争辩,而法官听了双方陈述后会做出裁决,判一方赢,另一方输。从这个角度看,那么调解与审判在所有主要方面看起来似乎都大不相同。调解是非正式、非对抗和基于当事人自愿的。审判重在体现正义,而调解看起来则重在维护和平。我们或许并不能够准确确定调解和裁决哪一个是人类历史上解决纠纷的主要方法。我们对调解大致都有一些相同的认识,但要确切地给调解下定义却并不容易。美国2002年的统一调解法在第2(1)条中规定,“调解”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调解人“促进”“当事人”之间的沟通和谈判,帮助他们就双方争议达成自愿解决方案。虽然现代法院附属调解经常被归功于美国近数十年的实践,但法院附属调解制度在中国早已
9、在民事审判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事实上,调解不仅在民事审判中被大量运用,它一直被中国作为解决所有纠纷的一种主要手段。调解经验已经被作为“东方经验”而广泛传播。统治者为了阻止诉讼,甚至故意增加打官司的难度和成本。清朝的康熙皇帝就曾说:“良好的处理方法是让他们诉诸于社区中的里老。”“对那些讨厌的、固执的、好讼的人,要让他们在公堂之上破产这就是他们应当领受的。”参见柯恩、王笑红译:现代化前夕的中国调解,载强世功编:调解、法制与现代性中国调解制度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就如Menkel-Meadow所言,“调解既古老,有和人类活动一样长远的历史;又崭新,是这项古老活动最近的“
10、新发明”。 Menkel-Meadow Carrie (2001), Mediation: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England Aldershot,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PPXIII有关审判和调解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存有一定的误解。尤其是在英美法系,人们一度觉得,法院或法官只能审理案件做出裁决。对他们来说,诉讼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法官在抗辩程序后运用已存在的法律规范来做出决断,赋予一方当事人法律权利,找出另一方当事人法律上的错误。” Martin Shapiro (1981): Courts: A comparative
11、and a political analysis. Chicago ; London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1.因而,不少人主张法院不应当插手调解,法院和法官只能去审理案件并作出裁判。一旦当事人选择了诉讼,法院就应当给他们一个谁是谁非的说法。今天,这种传统的看法被司法理论和司法实践逐渐抛弃,法官所作的远远不止于裁决一个纠纷。法官在诉讼中所扮演的角色已经发生较大的变化。 Jonathan Molot(2003): an old judicial role for a new litigation era, Yale Law Journal, 2003,
12、 Vol. 1, pp113.法官们不仅仅要对案件做出决断,他们还要解决问题,要给与当事人疗伤性质的司法正义而不是让他们深陷于输赢之争。现代司法要求法官让当事人自己成为程序的主人并可监督诉讼的结果,而不是一种突袭式的审判。总之,让法官判决哪一方当事人赢得案件已不再是诉讼的唯一目的。英国前大法官沃尔夫勋爵就指出,这种观点是基于更先进的理念,即法院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断案,而是为了友善地解决纠纷。 Ales Zalar(2006): litigation and mediation, pp2.因而,法院附属调解就应用而生。就司法实践而言,审判和调解的差异并不意味着它们就是互相排斥。相反,人们往往发现
13、审判和调解相辅相承。如果大量的纠纷能通过法院附属调解来解决,那么法院就能保持合适的案件数量,并将有限的司法资源集中在必要的审判上。另一方面,如果不是面临着最终判决的压力,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的意愿也会弱得多。因此,不妨认为,许多调解并不像看上去的那样都是当事人心甘情愿,背后都有裁决的压力;没有裁决的压力,当事人很难达成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方案。而裁决还给调解带来另一个好处,裁决所形成的判例法或先例,是当事人进行调解的重要参考。对于当事人而言,鉴于法院附属调解的一些明显的优点,比如调解过程的保密性及当事人对调解过程的最终控制权等,使得当事人往往对法院的非审判活动极感兴趣,尽管有时他们看上去更喜欢判决。
14、实证研究表明,其实对许多当事人来说,审判结果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审判也不是他们所向往的解纷程序。不少当事人不过是把审判当作一个要挟工具(以诉讼为要挟),使得对手在一个被称之为“诉讼谈判(litigotiation)”的过程中与己达成一个对自己有利的解决方案。 John Lande(2006): how much justice can we afford?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 NO 1,VOL.2006, pp223可以说,法院附属调解是法院诉讼程序和调解过程相结合的产物。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是这样。美国著名的法社会学学者戈兰特就曾说,过去
15、的二三十年里,在一些法域,在英美法系国家,调解已经间接或直接地融合进司法程序。 Roberts S and Palmer. M (2005): Dispute Processes: ADR and the Primary Forms of Decision-mak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315.在欧洲大陆,原本就有法官积极参加到友好解决当事人纠纷的传统,法院附属调解更是甚少被质疑。二、法院附属调解的不同模式:从法院外到法院内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来看,就法院附属调解的模式选择而言,分别由以下几种方式,即由私人服务商提供调解服务、法院专门职员提供调解服务
16、、专门的调解法官提供调解服务、主审法官提供调解服务。四种方式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即调解的主持人是来自于法院内部还是外部;是职业调解人、专门调解法官还是主审法官。(一)由私人的调解服务提供商进行调解在英国,法院通过向当事人介绍市场上的私人调解服务提供商的方法来提供调解。通过这样的方式,调解与诉讼相分离,当事人离开了法院系统,调解变成了诉讼外的一个选择。调解期间,法院的诉讼程序会暂时中止。一旦双方达不成调解协议或者任一方当事人退出调解程序,法院则将继续进行审判。因此,与德国、法国相比,英国有大量受过专业训练的职业调解人,他们有组织,权益也能得到很好地维护。但是目前存在僧多粥少的现象,很多调解人经过
17、培训后却没有足够的机会来实践。 Sir Brian Neill: a Mediation Medley, Arbit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bitration, Mediation and Dispute Management, pp5.(二)由法院内部设立的调解程序来进行调解在斯洛文尼亚,卢布尔雅那地区法院把调解工作当作法院的一项服务进行。调解是法院工作的一部分,由法院提供资金和人员保障,调解人也由法院培训和督导。 Ales Zalar(2006): litigation and mediation, Tijdschrift Confli
18、cthantering special issue 2006, pp1, 在荷兰,法院附属调解是由法院发起和管理的。但在上述两个样本中,调解人与法官是分离的。在澳大利亚,当事人可以自主选择法院内、外的调解人,但法院的主簿经常却处于一个独特的位置。由于他们有专业知识,又了解案件情况,在实践和程序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大多数当事人选择法院的主簿主持调解。有研究结论显示,这种实践和趋势已经被证明非常恰当、经济且卓有成效。 Jamie Wood(2004): Federal Court-annexed Mediation Seventeen Years on, Journal of Judicial A
19、dministration, Volume 14, Number 2, November 2004, PP98.(三)由专门的调解法官或者预审法官主持调解德国民事诉讼法典要求法院尝试通过协商来达成协议。第279条第(1)款规定:法院在案件审理过程的每个阶段都要考虑以和解方式来处理案件或考虑争辩的每个焦点。法院可以将希望和解的当事人转到任命法官或授权法官那里。因此,一般情况下,如果调解不成功,主持调解的法官不会再审理这个案件。目前看来,由调解法官主持调解在整个欧洲大陆似乎形成了一个趋势。在它的立法草案中,欧洲法官咨询委员会不排斥由法官充当调解人的角色,但强调调解法官不能是案件的审理法官。就是说,
20、如果一个法官正在审理某个案件,那么他就不能同时主持这个案件的调解。(四)由主审法官进行调解在中国和韩国,法院附属调解通常由主审法官主持,即使当事人不能达成调解协议,他们仍然将继续审理该案。在上述两国,经双方当事人同意,在案件审理的任何阶段,法官都可以展开调解:从诉讼程序开始到最后的听证,甚至在上诉期间,也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通常强调调解和审判分离的美国,尽管关于主审法官能否充当调解人的争论很激烈,一些主审法官仍然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 Dan Aaron Polster (2006):The Trial Judge as Mediator: A Rejoinder to Judge Cr
21、atsley, Volume 5, Issue 1 of the Ohio State Journal on Dispute Resolutions Mayhew-Hite Report.这种调解模式的优点和缺点都非常明显,对它的批判也非常多,人们一直担心这种调解模式可能会被误用。原因是法官在调解时可能会形成某种观点,而在其后的审判中会强加这种观点。另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就是,一旦法官建议了一个调解方案,当事人却不接受,这将是很不明智的,因为如果哪一方当事人特别反对法官的调解方案,法官对他的反应就可能不友好而对其不利。如果法官的观点是建立在当事人声称的事实基础上而没有程序保障,那么他的观点有可
22、能是错误的。在法官既作为调解员又作为裁判者的同时,调解的自愿性将被一个怀有偏见的法官彻底摧毁。如中国式主审法官主持调解经常为人所诟病的原因,即在于审判实务中经常存在的“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逼调”、“以诱促调”等强制调解现象的出现。总体而言,尽管仍然有批评认为,法院不应当去插手调解,但从主要国家的司法实践来看,法院附属调解已经得到了快速发展。在法院和调解组织的关系问题上,人们更加关注的是程序上的公正,而不是谁不能担当调解人。总结上述的四种方案,比较而言,由主审法官之外的主簿(或者法院调解员,预审法官或其他法院职员)作为调解人,似乎是较好的选择。与法院外部调解人相比,法院主簿或其他法院
23、职员能够充分利用法院的设施提供调解服务,切实降低成本,且能够迅速处理案件。而且,因为他们是法院的职员,对法院附属调解人的培训重任(及以后的服务质量)均由法院负责承担,因而容易得到当事人的信任,而当事人的信任是调解能够成功的重要因素。同时,与主审法官直接主持调解相比,当事人感到的压力会更小,有助于他们独立地做出决定,以确保调解的自愿性。三、当事人选择调解的方式:从自愿到些许强迫?调解必须基于当事人自愿,这是一直很少被质疑的调解的基本特征之一。即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选择调解来解决纠纷。但是调解程序的启动既可能是当事人提议的,也可能是根据法院的一个命令。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调解不应当过度影响案件的审理进
24、度和违背调解自愿原则,不应当去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但分析调解的案例后,却容易发现,有些调解似乎难以说是绝对的自愿。有人在分析法院附属调解中的强制和自愿的案例后,指出:“所有的调解都是自愿的,但有些调解显然自愿程度更甚。” Timothy Hedeen(2005): Coercion and Self-determination in Court-connected Mediation, the Justice System Journal ,VOL.26, Number 3, 2005.从各国实践来看,当事人绝对自愿要求进行调解的为数并不多,成功率也不一定就高。因为如果能轻松达成一致,或者就不
25、会形成诉讼;且双方当事人都可能回避主动提议调解,以免会被认为是对对方示弱。但完全强制性的调解也不常见。介乎完全自愿和绝对强制之间的法院附属调解似乎是一种较为普遍的选择。具体而言,当事人选择法院附属调解的方式有以下5种:(一)在正式立案前,当事人自己要求调解在此类调解中,当事人,尤其是原告,在向法院递交起诉状的同时,就要求先行调解。比如,韩国民事调解法就规定,法院附属调解程序可以根据法院的命令进行,也可以根据一方当事人的单方建议进行,而无需正式起诉。如果一方当事人不想破坏与另一方当事人的关系,或者希望通过简易、高效、经济的程序来解决纠纷,他可以在不进行正式起诉的情况下,提出直接调解的动议。这种情
26、况下,原告只需要先行缴纳正常诉讼费用的1/5。如果当事人间无法达成调解协议,案件将转入正式的审理程序。原告提出调解动议的时间被视为他开始诉讼的时间,此时他仅需缴纳其余的45的诉讼费用即可。因此,与直接就提起诉讼相比,直接提出动议要求进行调解并不存在明显的不利因素。在立案前即进行调解,既可节约双方当事人时间和金钱,对于法院也同样如此。且对被告方来说,成为调解程序的被告一方和成为诉讼程序的被告方,并没有什么不利后果。即使达不成调解协议,有关费用也可以按照法院附属的相关法律和法规进行处理。 Kwang-Taeck Woo: a Comparison of Court-connected Mediat
27、ion in Florida and Korea, Brook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Vol XXII:3, PP630-631.(二)案件移交法官前,由法院职员(非法官)听取当事人意愿后移送调解英国伦敦中区法院实验项目(CLCCPMS)是这种调解的典型。 Hazel Genn (1998): the Central London County Court Pilot Mediation Scheme: evaluation report, DCA Research Series 5/98.根据某种标准,自1996年至1998年的两年间,许多民事案件的当事
28、人或他们的律师都收到邀请信,邀请他们参加一个免费的、经专业培训的调解人主持的调解中去。如果任何一方当事人拒绝了调解建议,法院会写信告知双方因一方拒绝,调解无法进行。只有双方都接受调解建议的情况下,调解才能够进行。这种调解方法有多成功,很难衡量。在两年期间,共有4500个调解建议送给了当事人,但只有5% 的案件 (共160起案件) 进行了调解。在全部160起调解案件中,62/% (99起)案件成功通过调解解决。部分人士认为,这证明完全自愿调解在英国进行得并不顺利。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地区法院在1989年至1998年期间也曾推行过一个完全自愿且免费的调解项目,共有1,813起案件被移送进行调解。但仍有
29、85%的案件不能进行调解。在整个这个调解项目进行期间,累计的调解成功率略低于50%。 Edward J. Bergman and John G. Bicherman(1998): Court-annexed Mediati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Selected State and Federal Programs. Maryland Pike and Fischer, Inc. pp9-12.(三)法官建议当事人调解,当事人自主决定是否参加调解这种调解方式由法官倡议,但需经双方当事人同意。法官从其专业方面给与解释或鼓励,甚至可以发布一个非强制性的命令。只要有
30、一方当事人不接受调解,审理程序就要继续进行。这种调解的典型事例是英国高等法院商事庭的ADR命令。当法官认为ADR是比裁判更好的选择时,就会建议甚至发出命令指导当事人尝试ADR。而且如果当事人根据ADR命令未能协调解决,他们必须向法庭报告他们为何不进行调解,调解为什么不成功。这样,尽管法庭采取的措施并不是强制性的,但是法庭的命令还是对当事人造成了实质性的压力。一般认为,ADR命令对于最终达成协议有正面或者中立的影响。从1996年7月到2000年6月间,法庭共发出233件ADR命令,大约有略多于一半的当事人尝试了ADR。其中,52%达成了和解协议,5%在调解失败后进入了审判程序,20%在调解程序结
31、束后的一段时间内得到解决,悬而未决、结果不明的案件数为23%。英国商事庭的ADR命令的实践似乎表明,即使是由法官提议的,但一旦任由当事人完全自愿参与,则成效就不会太明显。当然,与伦敦中区法院的实验项目比较而言,当事人对ADR命令的重视程度显然甚于法院职员的调解建议信,调解的成功率也更高。(四)法官提议调解,无故拒绝调解的,可能是要受到惩罚此种调解与第(三)类调解的区别在于,在第(三)类调解中,双方当事人必须都同意调解才能继续进行,在第(四)类调解方式中,即使当事人不同意,法官也可以要求调解,当然当事人仍然可以随时退出调解程序。但是,这么做的话,他就可能面临经济上的惩罚。法官的法律依据是英国修改
32、后的民事诉讼法典的相关规定。现在已经有数起案例,不合作的当事人被施加了经济惩罚。一个典型事例是Dunnett v Railtrack (2001)案。在这样的案件中,赢得了诉讼的当事人仍然会面对经济上的惩罚,丧失了主张法律费用的机会。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沃尔夫勋爵对民事诉讼程序进行改革前,英国的司法实践倾向于不对拒不参加调解的当事人或者不合理拒绝调解协议的当事人进行制裁,但1999年的民事诉讼法典则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拒绝调解或者不接受调解方案的当事人,将可能会自己承担相应的诉讼费用和律师代理费用。(五)当事人必须先行调解,否则法院将不进行审判把调解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目前只是一些特殊种类案件
33、中实行。如美国Jefferson 家事法院监护权调解法规定如果当事人不能解决儿童的监护权问题,必须先进行强制性调解。德国民事诉讼法典15a规定的有关小额诉讼、侵害名誉权和邻里纠纷等案件,都要求在起诉前必须先经过调解。 Annie de Roo and Rob Jagtenberg :Work in progress: Comparative European Research on Court-encouraged Mediation. 中国的婚姻等案件,也是必须先行调解。这意味着此时的调解已经变成了一个强制性调解,而不是基于自愿。另一个极端的事例发生在菲律宾,根据法律规定,所有的纠纷在审判之
34、前都必须在一个调解中心先行进行调解。立案后,所有的审理工作暂停,调解失败后,审判才继续进行。 笔者于2007年4月1日在英国伦敦对菲律宾马尼拉Metropolitan Trial Court 法院 Marlo法官的个人访问。 (六)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从完全自愿到些许强迫综上所述,只有在第(一)种模式下,调解才是完全自愿的,在第(五)种模式下,调解就是完全强制。实践说明,由当事人完全自愿进行的调解成功率很低,或许是因为发生诉讼后,双方都不愿意通过选择调解来展现自身的弱点或者失掉自己的面子。而由法院职员,特别是法官建议进行调解,当事人或律师则更愿意接受。研究成果还表明强制程度与调解的选择和成功调解
35、的比率密切相关。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当事人受到要求调解的压力越大,他们选择调解的比率越高,调解成功的可能性似乎也越大。大部分当事人对调解的态度,处于绝对的自愿或者绝对的强制之间。从前述英国高等法院商事法庭,以及下面美国奥斯丁法院和澳大利亚联邦法院的经验和教训都表明,法院从最初奉行完全自愿的调解发展到倡导施加些许压力的调解。比如,德克萨斯州的奥斯丁市,从1987年到1995年,法院附属调解主要是自愿的,由律师们根据州ADR的规定提出调解建议。然而,从1993年开始,地区法院的民事法官开始研究其它办法鼓励实行调解。1995年,法官们采取了一项有关调解的综合性现行规则。经过两年的实践,制定了当地地区法
36、院规章第17章规定。自那以后,几乎所有等待陪审团判决的案子和所有不需要陪审团判决但审判时间预计超过半天以上的案子都自动转入调解;也即当事人必须将参加调解作为进入审判的先决条件。而且,几乎所有的案子可经由法官或当事人协议被送去进行调解。即便当事人一致反对调解,法院也可能认为该案不进行调解的理由足够充分。澳大利亚1997年修改后的联邦法院法规定,不论当事人同意与否,案件都可以转交调解。正如尼克尔森阐述道:“该法修正案赋予法院这项权利,即使当事人都不同意,法院仍可将一项诉讼案件转入调解;这项修正案做这样的规定,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即便一方当事人先前并不十分情愿,调解仍然可以取得丰硕的成果。 Ja
37、mie Wood(2004): Federal Court-annexed Mediation Seventeen Years on, Journal of Judicial Administration, Volume 14, Number 2, November 2004, PP92.即使不情愿参加调解,结果仍然是积极的。澳大利亚的经验显示出强制调解的结案率和满意度与自愿调解的比例是类似的。 Professor Kathy Mack, court referral to ADR: criteria and research, NADRAC, 2003.这个结论实际上表明,只要尝试进行调解,
38、就有成功的可能性,而总体而言,选择调解的案件越多,成功调解的案件也就越多。笔者认为,即使当事人不情愿参加,最终也未达成一致,调解仍能带来以下结果:当事人一致同意对事实的阐述、矛盾的焦点缩小、中间矛盾的解决以及对最终判决预期的减少等。而这些都有利于其后的裁判工作的顺利进行,以及当事人的息诉服判。对于中国所面临的申诉信访率居高不下的现状而言,后者似乎尤其重要。总而言之,在协商中的施加部分压力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有学者就认为,没有一点压力,当事人并不一定能做出合理的决定甚或是任何决定。当然,过度地施加压力也会侵犯当事人选择审判解决纠纷的权利。因而,适度地在告知和强迫之间,“诱使”人们采用调解
39、是可行的。 Tijdschrift Conflicthantering special issue 2006, pp3那个首次提出“多门法院”根据的哈佛大学弗兰克.桑德(Frank Sander)教授, 就曾形象地区分了“强迫当事人进行调解(coercion into mediation)”和“调解中的强制(coercion in mediation)”的区别。对多数法官而言,前者是可以接受的。有些人甚至宣称为了解决纠纷,强迫是必要的。 Frank Sander(2000): the Future of ADR, Journal of Dispute Resolution PP7-8于时,人们
40、开始反思调解的自愿性这一特征,并开始使用不同的定义。澳大利亚国家多元化纠纷解决顾问委员会对调解所下的定义即为:“调解是一个过程,其间,纠纷的当事人,在纠纷问题解决专家的协助下,致力于达成一个协议。”并进一步说明:“调解可以是自愿进行的,可以是根据法院命令进行的,也可以是根据已有的契约协议进行的。” Alan L. Limbury: an Australian Perspective on Some Topical Issues in Mediation. Arbitr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bitration, Mediation and D
41、ispute Management, Pp67.人们似乎越来越接受,调解的自愿性更多体现在对不满意的调解结果的拒绝,而不仅是对参加调解程序的自愿。四、影响调解是否成功的因素:说教、胡罗卜还是大棒?有多种原因可以解释调解为何会失败。作为一个富有弹性的程序,很多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参加法院附属的积极性和调解的成功率。除了案件的性质以及当事人的个性之外,以下因素都可能影响到当事人是否愿意进行调解以及最终能否达成一致。(一)经济因素的激励大量证据表明,在一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当事人选择调解的原因是诉讼费用太高。适当的费用激励措施,如调解不收费用或只收较低的费用,都可能会鼓励当事人自愿选择先行调解。
42、在一些国家中,对调解发生的律师费用也被包括在法律援助体系中,甚至申请法律援助的人必须先选择进行调解。害怕拒绝调解可能会带来费用上的不利负担也是原本不情愿参加调解的当事人参加调解的原因。当然,拒绝调解绝不意味着当事人丧失了要求由法院解决其纠纷的权利;寻求法院裁判途径解决问题的权利不能被损害。(二)法官对调解的兴趣一些事实似乎已经能够证明,法官们总有难以言明的权威来决定一个案件是否应当先进行调解。法官们总是能“左右”当事人选择调解。从中国90年代后期的经验看,不论调解的指标是多少,民事法官们总能完成调解指标。在刑事案件方面,Herbert M. Kritzer也发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在过
43、去的25年中,刑事案件的总量显著变化,但刑事法院通过正式开庭来审理的刑事案件数量却保持着稳定?最明显也是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刑事法院处理案件数量的能力有限,而法院总能把需要它审理的案件控制在其能处理的数量范围内。 Herbert M. Kritzer: Disappearing Trials?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p19-20.可以说,在法院附属的调解中,法官们(预审法官等)实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自己对调解的热衷或冷漠直接决定了调解能否进行、是否会成功。伦敦商事法院的试验项目和法国行政法院的试验项目均表明,一些法官热衷于调解,他们移送了大部分的调解案件,而
44、有的法官压根就不感兴趣,在他们眼里,或许没有需要通过调解解决的案件。在不少法院,个别法官有着比他的同僚高的多的调解率。这也似乎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有尚待研究不明确的结论认为,充分的研究说明,所谓科班出身的年轻法官调解成功率要低于经验丰富、但学历不高的老法官。(三)当事人和他们律师的意愿调解能否成功根本上还是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愿。Thierry Garby,世界调解中心论坛主席曾说过:“没有什么争端不可以用调解来解决。”关键在于当事人进行协商的意愿。有经验的调解人也认为,调解成功的几率并不在于案件的类型,而在于当事人的态度和见识。他们必须充分准备,有能力通过协商、在考虑双方利益的基础上找到解决纠纷的
45、方案。笔者所经历的一起事涉多个省部级单位、拖延数十年的土地所有权争议案件中,双方都主张对土地具有排他的使用权。包括笔者在内的许多法官都曾认为,这样的纠纷只能通过判决解决;但最终竟然通过争议双方在争议土地上建筑一幢高层楼房、争议双方分割楼层的方式,得以和解。当然,在移送和调解过程中,律师们的作用可能是“双刃剑”,即可能发挥积极作用,也可能发挥消极作用。律师可以让当事人知道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可能性有多大,也能很现实地让当事人明白案件如果庭审胜算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并对最终的调解协议提供建设性意见。但也有一些律师担心ADR会造成“收入惊人的下降”的ADR(Alarming Decline Revenu
46、e),而不情愿通过调解结案,而把案件拖入诉讼的泥潭。典型的案例即在于美国从事风险代理业务的律师,可能会为了得到巨额惩罚性赔偿而拒绝调解。(四)可供协商的空间影响调解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可供协商的空间。有时一些纠纷之间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很难协商;而另一些纠纷则涉及金钱的分割,如确定金额本身是不确定的,或者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补偿的,这类案件就容易通过协商解决。前者如伦敦中区法院的试验项目显示的人身伤害案件,此案案件由于赔偿标准具有一定的弹性,较易协商,占到调解案件总数的47%。后者则如公司间因经济纠纷。一些统计数据则显示,发生在公司间的争议则容易达成调解协议。 Hazel Genn (19
47、98): the Central London County Court Pilot Mediation Scheme: evaluation report, DCA Research Series 5/98, pp22.(五)调解的时机至于何时进行调解时机最佳,人们看法各异。有人主张越早进行选择越好,最好是在当事人形成观点、坚持立场前就做出决定。有人却认为每个冲突应该让其酝酿成熟,直至人们能决定不诉诸于法院,转而回到谈判桌上。在每个案件中,所有的当事人都同意,即便是在搁浅的纠纷中,总有一个时机,当事人能意识到进一步采取法律手段是毫无意义的,然后他们就能回到导致纠纷的最初的根本原因。另一方面,
48、总有人会使事情变得更糟,非要争个你死我活也不愿屈服。因此,何时进行调解并没有固定的时间表,而取决案情和调解人的技巧。五、对中国现行法院附属调解工作的启示从世界范围看,法院附属调解工作已经成为了解决纠纷的一个重要手段,甚至是法院的一项职能工作,对于中国而言,尤其如此。由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以及法院司法能力、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不足,似乎中国越来越强调通过调解、和解来解决矛盾,越来越强调“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而为了更好地做好法院附属调解工作,我们或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法院应当制定一些专门的政策和制度,让审判活动更加透明、公开,让法院的审理工作更加开放,更多融入当事人的意志。比
49、如给当事人提供更多的沟通的平台和机会,鼓励当事人在庭审前的对话、沟通和交流。更多地鼓励证据交换和庭前会议,并提供既决的同类案件的裁判供当事人参考,让当事人更多地了解案情,更客观地评估案件的裁判后果。正如波斯纳告诫我们的那样,“法律越不确定,以谈判解决纠纷的比率就越低。” 美理查德.波斯纳著:苏力译: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与传统的“和稀泥”或者利用当事人对事实和法律的一知半解进行被戏称为“坑蒙拐骗”式的调解不同,我们应当认识到,只有当当事人对事实和法律都有着较为客观的认识时,才更有可能自愿进行调解。这样的调解才不会有后遗症,才不会丧失对法院、法官的信任,才真正能实
50、现“案结事了”。其次,尝试在立案后立即由立案庭进行调解。英国、韩国和菲律宾的部分试验项目已经证明了此种尝试价值。而福建省三明三元区法院在2001年6月至2002年12月的一个试验项目也说明此种模式在解决民商事案件中的有效性。在这个项目中,法院共受理民商事案件1658件,其中1062件双方当事人自愿选择了庭前调解,占整个案件的64%;通过庭前调解结案458件,占全部起诉案件的26%,即在整个试验期间有四分之一的案件通过庭前调解审结。其中,有188件案件,在当日直接调解结案。 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开展庭前调解,便民利民为民,载陈明主编:立案审判实务与创新,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585
51、9页。再次,合理确定诉讼成本的承担模式以促进调解。诉讼成本既包括国家司法机关的成本,也包括诉讼双方当事人之间因诉讼的进行而产生的所有费用。如律师费用、证人费用、差旅费用。目前我们诉讼费用的承担主要还是败诉方承担,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完全由自己来承担,即使是胜诉方也可能被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而付出巨大的成本。而为了对当事人的不当诉讼行为进行惩诫,避免司法资源的无谓浪费,我们可以要求那些无正当理由拒绝和解或者是恶意诉讼的当事人承担因此而多支出的诉讼费以及补偿对方当事人的额外费用,通过灵活地减轻或者加大当事人的诉讼成本来促进调解工作。并通过“胡罗卜”和“大棒”并用的政策来促进法院附属调解的全面开展,以减
52、轻法院裁决案件的负担和压力。第四,赋予当事人申请主审法官的回避权,来保证调解结果是建立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的。我们可以劝导、引诱甚至强迫当事人参加到调解程序,但我们不能让当事人在不自愿的情况下接受调解结果。我国的法院附属调解是由主审法官主持下进行的,从长远看,实现主审法官与调解法官相分离或许是一种可能的选择,或者由法官助理而不是由主审法官主持调解。但在目前主审法官包揽调解和审理工作的现实情况下,我们可以赋予当事人对先入为主或者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结果的法官申请回避权,来平衡调解自愿与法官建议间的关系,即如果调解是由主审法官建议并由主审法官主持的,如果当事人认为主审法官在调解中存在不当的言行、或者
53、有明显的偏向,他就可以在随后的审判活动中,申请主审法官回避。最后,在大力倡导法院附属调解的同时,我们也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调解不是一剂万能药,它有着十分明显的副作用。这在尚处于法治初级阶段的中国或许尤为明显。 参见耿宝建:“定纷止争“莫忘“定分”对调解热的冷思考,载法学2005年第8期。因此法官或法院不能放弃对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即便协议是在当事人自治的基础上达成的,法官也应有权决定其是否合法,是否无效,特别是当这种协议可能涉及第三方利益或公众利益时。毕竟,除了解决纠纷之外,法院的另一个重要的功能即在于宣示法律,践行法治。而在司法公正缺失、司法权威不够、司法公信力较低或腐败浮云笼罩的国家中,这尤为重要。同时,调解制度与其他解决纠纷的制度一样,要想真正发挥其功用,无疑仍然有赖于人的因素,最终取决于主持调解的法官、调解法官或者其他调解人的综合素质和其对法治的信仰。如果一个国家没有法治的传统或人民的法律权利有限,“向他们提供调解会被视为给了他们一个替代方案的诱饵,却延缓了一个真正公正的司法体系发展的步伐。” Tijdschrift Conflicthantering Special Issue 2006,pp511
- 温馨提示:
1: 本站所有资源如无特殊说明,都需要本地电脑安装OFFICE2007和PDF阅读器。图纸软件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压缩文件请下载最新的WinRAR软件解压。
2: 本站的文档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图纸等,如果需要附件,请联系上传者。文件的所有权益归上传用户所有。
3.本站RAR压缩包中若带图纸,网页内容里面会有图纸预览,若没有图纸预览就没有图纸。
4. 未经权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将文件中的内容挪作商业或盈利用途。
5. 装配图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保护处理,对用户上传分享的文档内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编辑,并不能对任何下载内容负责。
6. 下载文件中如有侵权或不适当内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立即纠正。
7. 本站不保证下载资源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时也不承担用户因使用这些下载资源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