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五代十国南北朝
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五代十国南北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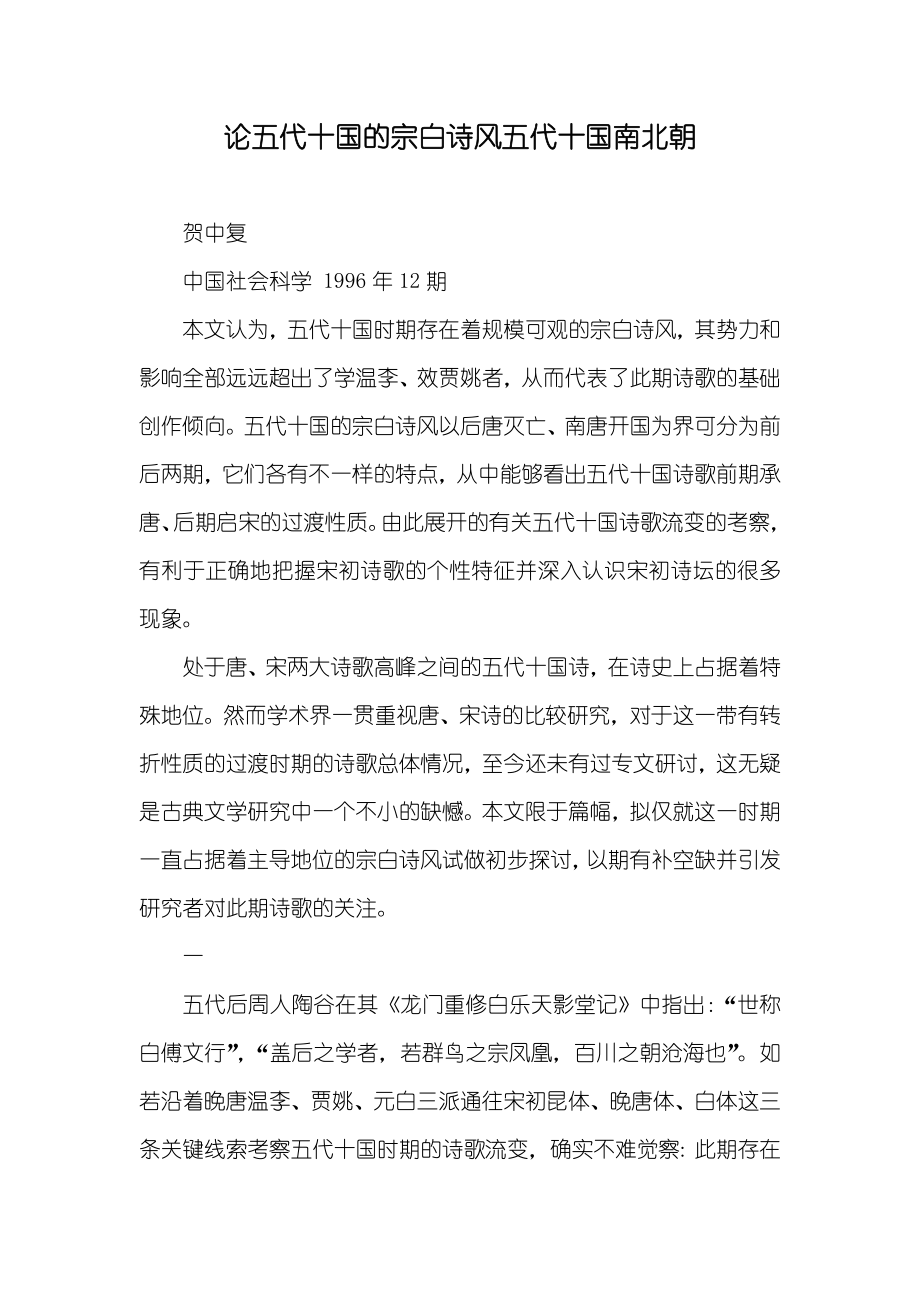


《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五代十国南北朝》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五代十国南北朝(22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论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五代十国南北朝 贺中复中国社会科学 1996年12期本文认为,五代十国时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全部远远超出了学温李、效贾姚者,从而代表了此期诗歌的基础创作倾向。五代十国的宗白诗风以后唐灭亡、南唐开国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它们各有不一样的特点,从中能够看出五代十国诗歌前期承唐、后期启宋的过渡性质。由此展开的有关五代十国诗歌流变的考察,有利于正确地把握宋初诗歌的个性特征并深入认识宋初诗坛的很多现象。处于唐、宋两大诗歌高峰之间的五代十国诗,在诗史上占据着特殊地位。然而学术界一贯重视唐、宋诗的比较研究,对于这一带有转折性质的过渡时期的诗歌总体情况,至今还未有过专文研
2、讨,这无疑是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不小的缺憾。本文限于篇幅,拟仅就这一时期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宗白诗风试做初步探讨,以期有补空缺并引发研究者对此期诗歌的关注。一五代后周人陶谷在其龙门重修白乐天影堂记中指出:“世称白傅文行”,“盖后之学者,若群鸟之宗凤凰,百川之朝沧海也”。如若沿着晚唐温李、贾姚、元白三派通往宋初昆体、晚唐体、白体这三条关键线索考察五代十国时期的诗歌流变,确实不难觉察:此期存在着规模可观的宗白诗风,其势力和影响全部超出学温李、效贾姚者,诗坛也所以展现出百鸟朝凤、百川赴海的局面。五代人学温庭筠、李商隐为诗已在侧重学温,并由重温之乐府逐步转向重其清俊淡远的律诗。尽管“以秾致相夸”的温、李
3、诗仍然从不一样方面影响着五代诗人的创作,而终五代一世,并没有产生出堪称温、李后劲的艳体诗人,更无从形成追风温、李的诗歌流派。相比之下,此期追踪贾岛、姚合的一派虽诗人较多,实力较大,其诗风较之晚唐也有显著新变,但诗人的穷居山寺僻壤、远离政治斗争和诗作的取径褊狭、单调贫弱,又终不能使其成就为五代诗歌的主流。从多方面看,五代诗风最盛者当推宗白一派:就此期关键诗人70家计,追风白居易的不下五分之三,在今存诗200首以上的11家中,可归为此派者竟多达8家,且均为五代著名诗人;至于其所覆盖的地域,较集中于楚之衡山、吴之庐山的贾、姚派要广泛得多,南方前后蜀、吴越、闽、南唐和中原后唐、后周全部涌现出规模不一的
4、创作群体,集中表现着五代诗人群体性特征;五代时白居易的诗文集东林抄本在吴和荆南诸国流传,影响深广,帝王诵白诗以诮臣下,社会上还出现了以“白乐天、罗隐二人诗百首”为“扎刺”的现象;白诗为选家推重,后蜀韦穀编才调集就以白居易长篇排律6首和秦中吟十篇冠首,而就刻版印刷初兴时蜀中即开印宗白名家贯休禅月集及白氏六帖,亦可得悉五代宗白之风的盛行。尤其是此期宗白诗人以据有一定政治地位、文学主张明确、创作活跃而含有较大凝聚力、感召力。唐彦谦之孙陶谷、名僧齐己论诗全部渐重白居易,不论就唐末原学温效李的韩偓、罗隐以后全部转向学杜宗白而言,还是从五代贾姚一派由重贾转重姚再向宗白趋近的演进轨迹来看,宗白诗风在五代起着
5、主导作用,集中表现着一代诗歌的基础创作倾向和转折特征是肯定无疑的。五代诗人的“宗白”,当然不排除取法元稹,不过自唐末始,“元、白两不相下”的情况确实发生了承唐启宋的新改变,即白居易在诗界的地位已显著地高出元稹而独居一派鳌头。唐末张为诗人主客图奉白为“广大教化主”,而元仅得“入室”;五代人所撰笔记唐摭言等通常称扬白居易的人格诗品,而以艳诗见长的元稹已极少为人单独言及。官修旧唐书之元白传论虽把元、白一并推为元和时期的诗坛盟主,但传文中所肯定元稹的是她和白氏间的往还赠答诗和入乐歌诗,不但对元的褒奖远不及白全方面而突出,如据“宫中呼为元才子”之类的记述,史家于元还不无微辞,所以传论又强调指明:“就文观
6、行,居易为优”。唐末五代在对待元、白上的这一新变表明,此期尊白之风的兴起是晚唐李戡、杜牧诸人斥元、白诗“纤艳不逞”、“淫言蝶语”以后,诗界对元、白人格诗品认真审阅权衡的必定反应,是唐末重教化、反轻艳文学思潮兴起后在学元、白上的详细表现,即“学淫靡于元稹”受到抑制,“学浅切于白居易”得以倡扬。经唐代诗歌极盛以后,诗苑中仅通俗一体还未得到充足发展,宗白诗风之因此终五代十国而不衰,愈演愈烈,更主要的原因之一恰是白诗之“俗”和此期诗歌取向之“俗”的拍合。五代俗文化的全方面空前兴盛,致使诗歌的通俗化流向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不但大批出身寒微的诗人普遍熟悉俗事、俗情、俗语,讲话为诗实难脱俗,而且原本身为舞枪
7、弄棒之武人的帝王又几乎无不喜好、提倡通俗诗,杜荀鹤、卢延让等诗坛名家因献诗“易晓”而深得厚遇且不次擢升,在广大文人中间造成一个颇具诱惑力的创作导向。极重诗歌社会效果的一些诗人为追求“闻之者虽不知书,亦释然晓之”,使所刺武夫酷吏“变色”、“畏之”,更把白诗的“见者易晓”、“闻者深诫”奉为恪守的创作信条。而中唐以来江湖间广泛流传的白氏俗体诗,又为五代十国众多南方诗人提供了取法的直接依据,即使以文雅著称的南唐君臣也深受溉润。五代宗白风盛至为关键的是,白居易作为唐王朝盛衰转变期新兴庶族的诗歌大家,其为人、为诗集中表现着历史转折期的世俗思想和创作特征,充足展现出封建士人思想性格的双重性和人生、创作历程的
8、阶段性:既尊奉儒学,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既力行“达则兼及天下”,更主“穷则独善其身”;现有议论讽刺时政的讽谕诗,又有“知足保和,吟玩性情”的闲适诗;既长于为尊古后学所倾重的古体诗,更长于时兴的近体。“立身百行足,为文六艺全”,其人格和诗品无不堪资后世取法。追踪唐人的五代诗家正是从其特定历史时期的生活感受、创作追求出发,在大力标举白氏为人的同时从不一样方面效法白氏为诗的。五代十国的宗白诗也所以大致可依取向、诗风的相对差异,以后唐灭亡、南唐开国为界分作前后两期。二五代宗白诗风的兴盛始肇于唐末。前期宗白诗人大多是由唐入五代的名家,面对唐末“奢靡极,衅孽兆,世衰而诗亦因之”的社会、诗坛现实,她们
9、几乎无不做出较她派更敏锐、更强烈的反应。吴融序贯休禅月集,大力提倡白居易讽谏诗50篇的教化精神,以反李贺以来“洞房蛾眉、神仙诡怪”的诗坛风气。至黄滔作答陈磻隐论诗书,更非议当初“郑卫之声鼎沸”的“今体才调歌诗”,因强调诗歌的社会作用而于唐代四大家中尤重白居易,并继皮日休诸人以后,针对晚唐李戡以来的“以粉黛为乐天之罪”公开为白诗辨白。关键取决于揭露现实昏暗,反应民生疾苦和反对鲜涉社会痛痒的轻艳诗风的需要,在舆论界推崇白诗政教精神、排抑浮靡倾向以亲密诗歌和现实关系的同时,于唐末皮日休、陆龟蒙诸人讽刺小品文兴盛之际,在诗歌创作上宗白之风也对应崛起。诗大家或痛感唐朝丧乱,民生涂炭,出自“致君活国济生人
10、”的实用动机,效法白居易“先向歌诗求讽刺”;或以诗道为己任,经过“诗本国风王泽,将以判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的深刻反思,深入明确其创作的社会职责。和无官无禄者“则著私书而疏善恶,斯因此警当世而诫未来”相一致,“仕若不得志”者每把白居易“处世似孤鹤,遗荣同脱蝉”视作为人为诗的“龟镜”。至于追风温、李的艳体诗人,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灵受到强烈震撼者,更不能不面向严酷现实,重新调整其创作方向,即使是原学贾、姚为诗的一些隐逸文人,也不能不受朝代更迭大潮的波及,伤叹风雅沦丧,感世伤时。总而言之,在唐、五代之交,诗大家纷纷从不一样路径走上宗白一路,结聚于尚实尚俗的白氏大纛之下。其间“秦妇吟秀才”韦庄堪
11、称该派的先行者,而以杜荀鹤、贯休为关键的两个主要群体的形成,则是此期宗白诗风兴起的鲜明标志。和中晚唐不一样,五代前期的宗白诗人关键是居官失志者或求官不得者,为时局所迫,大致自昭宗天复元年起,其身心已显著地远离唐京而依附于割据强藩的诸王幕府或寄寓其统治地域,她们的生活、思想、心态全部带有从统一到分治和新旧朝代更替的时代特征。自唐末丧乱、皇帝播迁以来,文大家饱尝了避难流离之苦,伴随对朝政昏暗和社会症结的感知日深,其“致君活国”的信念虽因时递减,而从个人切身遭际和“济生人”出发干预政治现实,仍不失为一股主要思潮。改朝换代造成的思想意识的重建,突出表现为不固守往常忠君不二的为臣之道,其对待当朝的态度也
12、因较少希求而更趋客观。此期文人“怀才不得志”之关键决定于政局动荡,不少平生主动进取的志士却终不免长久失意沉沦,个人命运和时代命运紧紧扭结在一起。“九土现在尽用兵,短戈长戟困书生”,置身窘境的文大家深感救时无策,自悔奔波求名,避世心理普遍存在,却又往往认为“此心非此志,终拟致明君”,甚至唐朝的覆亡也没能使其用世理想完全归于幻灭。所以这类诗人进入五代以后,其批判现实的精神虽或有削减,但一度晚达、官至显位者并未今后醉心享乐。韦庄、黄滔诸人全部曾佐助新王开一国局面,隐居不仕、广结僧道者也并非“逢人不说人间事”的“人间无事人”,即使隐钓延寿溪的徐夤也以不能忘怀现实而迥别于贾岛者流。此期宗白诗人在唐亡之前
13、大全部未得结集于朝,唐亡以后又各居方国,一直展现着散播状态,其视野不免收敛褊狭,但较其前辈更靠近下层民众和地方文化。正因如此,在成就斐然、极盛难继的唐诗面前,五代前期宗白诗人在创作上并没有犹豫不前或亦步亦趋,其承唐变新关键出自对咸通以来“风雅道丧”的不满,在主学白居易的同时兼取多家之长,发扬地方文化传统,以反拨、博取求创新,在“古”和“今”、“复”和“变”中求发展。在把白派诗风沿着实用性、通俗化的轨道推向前进的过程中,因为诗人生活经历、思想情怀、艺术情趣、天资才力的相对差异,其创新发展以巨细不一、各有偏重而展现出多样性、多极化特征。由白居易诗的多方面反应社会现实,走向集中揭露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
14、和政治昏暗,作诗“务趋条畅”,并演其为五代一派诗法。在这方面导夫先路的当推“香山之替人”韦庄,罗隐亦属同道,如就韩偓入闽后诗以“顿趋浅率”而“逗宋格”看,或亦趋近于此。这些早年曾作艳诗的名家,在时代大潮强烈冲击下宗白新变的突出特点是兼由李商隐入门学杜甫,在白、杜诗风的融合中求创新。韦庄在黄巢起义军破长安时作诗描述亲友相失、强藩异心,韩偓被贬出朝所作“昌言直斥”祸国党人,无不从个人痛切感受出发暴露当朝社会政治的昏乱并间或嘲讽。在撮聚白诗之闲适情趣和杜诗“鱼吹细浪摇歌扇”的笔法,把绝句体推向精工境地的同时,更显突出的是同得杜、白之“直遂”,以周详明直、语近情深反拨温、李诗的曲隐晦涩。尤其是韦庄名篇
15、秦妇吟、陪金陵府相中堂夜宴、观浙西府相畋游和曾被误为白作的南阳小将张彦硖口镇税人场射虎歌等,汲取白居易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的叙事笔调和白描手法,寓讽谏于描写,融抒情于叙事,在白诗层层展开、步步推进法的基础上形成依次抒写、条贯流畅、通浅平易的新风,以下开一派诗法而影响了中朝符彦卿、西蜀卢延让和南唐徐铉、郑文宝等多人。主学白居易新乐府之讽谏精神,并将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导向极致。同出吴越的名家罗隐、贯休,上承唐末皮日休、陆龟蒙、聂夷中等学白为诗的现实主义诗派,较之韦庄诸人更重诗歌的实用性并能汲取吴越诗“讲话横肆”的地方传统作风,而成为五代宗白一派中个性鲜明的一支。罗隐诗不但从李商隐入门学杜甫“坚
16、浑雄博”而独得“酣情饱墨”、“调高韵响”之风调,更长于融合温之刺时和白之讽谏两大特征,“缘情必务于刺时,体物无忘于谏猎”,以其咏史及感弄猴人赐朱绂等近体诗极富批判性、戏谑性而成为五代讽刺诗人的经典。贯休尤重白居易诗文的“实可警策未悟,贻厥未来”,“为文攀讽谏”,选择“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大力创作抒写自由的乐府诗,指斥酷吏、佞臣、阔少,为兵卒、樵夫、蚕妇言苦,其代表作阳春曲甚至大声疾呼,为民请命。贯休、罗隐入五代后除写作讽谏诗外,全部有颂扬新君治国理民功业的诗章产生。“美”以“劝乎功”,“刺”以“诫乎政”,以颂圣劝诫展现出五代宗白诗不一样以往的新面貌。罗隐诗虽和韦庄同“务趋条畅”,却更多议论说理
17、,其“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劳为谁甜”一类,以事理、物象相互生发而令人深思。而贯休在把儒家仁爱和佛家慈悲相结合的同时,汲取唐代诗僧王梵志、寒山、拾得通俗说理的禅偈作风和韩、孟诗法,深入牢靠确立了“以议论为诗”、“以文为诗”在五代宗白诗的地位,不但使古乐府更显“高古”,近体诗也更朴直、明快、自由、开阔。只是贯休作诗过分强调义理,“率意放辞”,把白诗的“意激而言质”导向使气不避叫嚣,甚至剑手怒骂,在粗疏、俗俚、芜杂上全部较罗隐等宗白诗人走向更远的极端。五代罗隐、贯休的追随者突出表现为地域性、群体性特征。大抵说来,以钱氏公族为关键的吴越诗人推重、效法罗隐:钱鏐诗称扬邦民并和之同乐,钱倜作陈国诗以淫奢
18、亡国自警,钱弘亿有规讽钱倜诗。尤其是钱鏐取法本土民歌作吴音的还乡歌和命罗隐续写役卒的无了期,一致表明吴越君臣对通俗诗下偶俗好的导向,大量使用方言、俗语咏本土风物,致使吴越宗白诗风深入走向大众化而成为五代俚俗诗的经典。贯休诗对吴越处默、延寿、赞宁诸僧也启示显著,不过受其影响最大以至形成地域风气的却是西蜀:贯休弟子昙域诗“亚师之体”,蒋贻恭诗尤“巧于刺讥,蜀人畏之”,顾敻、归处纳、刘隐辞等多人发扬贯休、韦庄的宗白讽谏精神,使嘲讽豪奢贪暴的大小统治者成为五代蜀诗一大特色,并进而把嘲讽对象扩展到通常人或事。和此相关,因为戏谑性和口语化的强化而带有更多市井平民阶层的审美情趣,伴随议论化、散文化的普遍利用
19、,其粗俚直露无异“打油”,已到了非转向不可的地步。不过,贯休羽翼卢延让承白之俗多著“平常轻易语”,在描取日常习见现象上务出新意,最终形成了为宋初重视的一体。承袭白居易感伤诗,集中抒发乱离时代有志无时、怀才不遇的苦衷,深入演绎白氏“平而易”作风和比兴传统。此路作为一个自觉的创作追求,以闽诗人黄滔、徐夤最为突出。互为诗友、均长律赋的黄、徐一致尊白、学白,徐夤认为,“诗也者,能够刺上而讽于时”,并表示“余欲编田歌于乐府,上闻于至尊”。然而她们作诗却不如韦庄、贯休诸人外向,长久失意及唐王朝的“中兴”无望,迫使其着重学取白诗的自伤和伤时相结合,重视抒写那个特定时代所触发的身世之感。黄滔在漫长的求第求禄时
20、期所作的大量“言怀”、“书怀”、“寄怀”、“旅怀”或唱和诗,多属以诗代书、向人求荐之类,在诉说自己的窘况和苦衷时,“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期“常人俗士闻见之亦宜感动”。其诗寄林宽、逢友人等既不雕琢藻饰,也不气激叫嚣,而是流利圆润,淡而有味,在白诗“平而易”的基础上,别辟平淡自然一路,进而形成其“清淳丰润,若和人对语“的作风。和黄滔相较,“平生欲献匡君策”却又长久过着隐钓和清客生活的徐夤,在宗白上则别有创获。和她献诗触讳险致大祸相关,其诗着重学取白居易的托物言志,有追和白舍人咏白牡丹诗,所作大量诗篇咏及云、雨、鹭、鹤、松、梅等近70种,分类排比制作,力争把自己不一样凡俗的高洁人格和对污秽现
21、实的鄙弃外物化、详细化。尽管咏灯、咏帕等未免失之琐屑,却终以重视兴象和性情的结合确立了咏物言怀诗在五代诗歌中的突出地位。黄、徐宗白诗所展现的新变经翁承赞、郑良士、詹敦仁等闽中诗人的共同努力,在诗之明白如话、比方象征方面全部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境地。借鉴白居易诸人诗的内容、形式改造诗体,融合古今,进而提升古、近体诗的表现力。罗隐、贯休等在这方面全部有所尝试,而包含杜荀鹤、张乔、张、王贞白、郑谷和杨夔、殷文圭等在内的吴国诗人贡献尤为突出。这一诗人群大抵由学姚合转向宗白,反轻艳,倡师古,益重“六义之旨,二南之风”,在宗白变新上致力于两派诗风的融合及学白和师古的统一。受昭宗“中兴”的感召,杜荀鹤力主诗当“
22、外却浮华景,中含教化情”,其诗“诗旨未能忘教化”,即使以诗哭方干,也着眼其诗的“关教化”、“破艳冶”、“擒雕巧”。她全力写作近体诗却能远承诗经国风,近取以兴讽见长的初唐陈子昂,视近体如古体,题其七律山中寡妇、乱后逢村叟为时世行把白居易乐府诗“唯歌生民病”的社会内容引入律绝之中,以收取“使贪吏廉,邪臣正”的社会效果。这就大幅度地突破了杜甫以来用近体诗抒写情怀的成法,扩大了白居易乐府的势力范围,提升了近体诗表现生活的能力。和此相关,杜荀鹤作近体还往往不为声律所拘,多用虚字,这种在通俗化、散文化冲击下的新变,还突出表现在把晚唐人的“不避俚俗”变为对俚俗的自觉追求,效白取法吴地民歌,一句之中喜用二字相
23、叠法等全部颇有“古歌谣之遗”,故殷文圭称其“二南新格变风骚”。宋人严羽于唐末五代独标“杜荀鹤体”,“九华四俊”中的张乔、张为诗也近杜荀鹤,不过张乔早逝,张又仕官西蜀,在吴影响显著的是杨行密始称吴王之际辞官归乡的王贞白和郑谷。王、郑为诗致力于元和以来奇险怪异、感伤闲适两大流向的汇聚,更倾向抒写内心世界。在杜荀鹤变新近体的同时,王贞白对古体诗所做的对应改造集中表现着这一倾向。王贞白诗“臻前辈之阃阈”,她较杜荀鹤在传统上更重陶渊明、李白的古诗,于白派中则倾重诗含古意、思难辞易的吴籍名家张籍。她学和白居易新乐府精神相通的张籍古乐府,其新变特点在于把张籍征妇怨、妾薄命、别离曲等写战乱言疾苦,转为以湘妃怨
24、、妾薄命、有所思等自传失意苦衷,用长安道、洛阳道等自写道途流落、入仕无门,为数更多的边城曲则重在表示壮志难酬、漂泊思乡之情。如此把当初近体诗所写内容扩展到古体,致使五代诗着重抒发主观情怀的特征愈加突出。而王贞白的诗友郑谷作为从李频、方干学姚合转向宗白的诗人,面对“浮华重发作,雅正甚湮沦”的诗坛现实状况,推重薛能“淡薄虽师古,纵横得意新”的师古变新,取法元、白被贬后所作的“江南人士,传道讽诵”、“观其流离放逐之意,靡不凄惋”的感伤诗,致力于反应社会现实和抒写情怀的结合,把个人流离和社会动乱、个人怨愤和时代悲愁融合为一。她全力写作的近体诗力避贾岛之寒涩而扬姚合之清远,得白氏之浅切又力避其粗俗芜杂,
25、尤其是郑谷作诗“远继周南美”,承传白居易等取法江南俗体诗的作法,在长久漂泊中尤重汲取江南、巴蜀民歌并精心提炼,在意象组合、修辞利用、遣词造语和色彩声韵等多方苦心经营,从而形成其“清婉明白”的独特诗风。吴国宗白诗风演至孙鲂、沈彬又有新变。孙鲂“从郑谷游,咏诗颇有郑体”,却更倾向抒写宴间唱酬,咏花木山水,其间洋溢的士大夫生活气息和白居易闲适诗相近。至此,喜用对举、叠字和重设色等全部已成为吴中宗白诗的自觉追求。而“天性狂逸”的沈彬作诗则更近王贞白,风雅比兴,颇有古风。其结客少年场行、入塞二首等乐府诗,在情调悲凉多奇气上又和贯休诗一致。孙鲂、沈彬和中书侍郎李建勋同居金陵,共结诗社,孙、沈不尽相同的诗风
26、全部直接影响了南唐开山诗人李建勋的创作。三五代诗歌演至南唐开国,始由前期的承唐转为后期的启宋,究其关键,则取决于宗白诗风的转型性新变。五代开启三十年以后,诗坛发生了堪称宗白新变之先决条件的两大改变:其一是诗人的成批代谢。杜荀鹤、罗隐、韦庄、贯休、黄滔等由唐入五代的宗白名家前后辞世,继之而起的基础全部是唐亡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代新人,生活、思想和创作追求的相对差异,致使相互之间展现出鲜明的代沟;其二是诗坛多中心状态的改变。五代后期,一些地域性诗坛因宗白关键诗人的逝去或政局的动乱而陷于涣散、停滞状态,后蜀、吴越诸国虽仍有欧阳炯、钱倜等在,亦未免较前逊色。伴随五代后期经济、政治、文化重心的形成和诗界名家
27、的相对集中,独领风骚的诗坛重镇崛起于南唐,从而为后期宗白诗风的转型性新变从多方面提供了有利条件并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吴国诗坛基础上直接建构起来的南唐诗坛,因为没有遭遇改朝换代的战火焚劫等很多原因此得以快速壮大。李建勋、孙鲂、沈彬诸人的吴中金陵诗社至此虽因沈彬的归乡和孙鲂的早逝而解体,但李、沈间的诗筒往还仍然继续了较长时间,李建勋更官至宰相并成为南唐诗坛的关键奠基者。吴时已崭露头角的冯延巳、冯延鲁、徐铉、韩熙载、江文蔚、乔匡舜等人,全部成了南唐诗苑的宗白骨干。尤其是中主李璟攻灭闽、楚后,早已名动中朝的诗人孟宾于及廖凝等前后入金陵,并得到李建勋、徐铉、韩熙载等诗坛巨擘的一致推重,相互唱和,孟宾于还有
28、金陵、玉笥、剑池诸集连连问世,于是继唐末以来吴中诗人流寓入楚、闽中诗人就学于吴以后,宗白诗人及其诗风今后在长江下游较大范围内展现出深入聚集、融合的新局面。和此同时,不但晚唐以来温庭筠之轻艳和贾岛之僻涩等诗风痼疾在诗歌流变中已暴露得愈加充足,而且五代前期不一样地域的诗大家在矫弊宗白方面所做的种种尝试和努力,其优劣长短也日趋显著。其间除流于淡而无味者外,尤以失之粗疏一端最为突出并引发诗界的不满。贯休诗反轻艳、倡教化而往往归之叫嚣,其“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以“太粗”而被讥为“失猫诗”,受白氏、贯休“辞繁言激”影响的前蜀庾传昌诗则“伤于冗杂”,卢延让诗俗不可耐处也被孙光宪诸人讥为“猫狗诗”、“打脊
29、诗”,杜荀鹤诗“今日偶题题似著,不知题后更谁题”以太类禅偈也被讥为“有四蹄”的“卫子诗”。这无疑全部为后期宗白诗人的深入探索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依据和反拨求新的出发点。有心“恢复高、太之土宇”的南唐君臣每以承唐自任,然而其“中兴唐祚”的实质已经有别于昭宗“中兴”,堪称后周南征、北宋统一之前奏。其山河重圆、再造新局的变革精神也因之表现于很多方面。为革除五代前期的“武人政治”和“右武戏儒”之风,南唐极重文治,把“举用儒吏”奉为一直一贯的基础国策,采取多个方法延揽四方学士和培植本土人材,致使一大批庶族地主知识分子伴随文人地位的空前提升而官至显位,进而形成了前期不曾有的以上层重臣为关键的庞大宗白诗人群体。
30、她们在思想界拼力扭转以往“以经艺为迂阔”的看法,远绍中唐,兴复儒学,博综经史;在文学领域则主动提倡重师古,祖风骚,宗汉魏,以矫咸通以来诗歌“雅道陵缺”之失,自始至终针对不局限于南唐的文坛现实状况寻求变革,整饬文风,既排抑纤丽轻靡,更抵制僻涩寒薄,在宗白上其创作追求较之前期颇多新变。由主学白居易诗扩展、提升为取法中唐“元和体”。五代前期虽也有黄滔等部分诗人偶师“元和”,但至后期南唐,效法安史之乱后“中兴”时期的“元和体”才更自觉,更广泛。除在理论上标举“元和体”外,以诗取士也肯定“追踪元和之际”的文风,文大家更将其作为努力方向主动付诸创作实践,故后人每称南唐人诗有元和之体。据张洎张司业诗集序指明
31、张籍诗“古风最善”以后所说:“元和中,公及元丞相、白乐天、孟东野歌词,天下宗匠,谓之元和体”,南唐人所提倡的“元和体”和唐代李肇诸人所指有别,着重指元和间张、孟和元、白的古体诗,“上可稗教化”、“下可理情性”的乐府歌行。尽管就南唐宗白诗人的创作看,她们取法“元和体”并不排除元白诸人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和杯酒光景间的短篇律绝,张洎为张籍、项斯诗集作序也对其吟咏情性、描摹风物的近体诗给予肯定,不过持守儒家政教文学观的南唐人,在理论上更重视元和古风,以求变革唐末以来“风雅道丧”的诗界情况是肯定无疑的。如就张洎重视不一样于白居易明陈直斥、气激言冗的张籍诗看,尚可大致得悉南唐人宗白有别于贯休诸人的取向。由
32、学白居易诸人的讽谕诗转为集中学其感伤、闲适、杂律诗。五代前期宗白诗人虽也学白氏感伤、闲适之类,却以学其讽谏显露特征。后期以二徐、二冯等枢要大臣为主体的宗白一派虽主张恢复儒家诗教传统,但南唐毕竟不是中唐,也不一样于五代前期,标举“词必有关教化”,却不提倡以诗刺上,主“物情上达,王泽下流”,重“厚君臣之情”。尽管冯延鲁等极少数人也作讽谕诗,而绝大多数宗白诗人并不如此实践。造成这种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之差距的关键在于,此期诗人没有前期贯休、罗隐等身历乱亡的深刻生活感受,南唐“中兴”本身更潜含着衰微基因,作为政治舞台主角的君臣又缺乏政治家的远大怀抱,所以一旦南唐暂短的兴盛期逝去,面对攻闽征楚造成的国力虚
33、耗和内部党争的倾轧不已,诗大家普遍深感力不从心,理想幻灭,其兴邦的社会责任感也急剧减弱,这就不得不由重外物事功快速转为重内心修养,更多地思索个人命运和人生哲学。在“以立言为功业”、自保荣禄的同时,其诗歌创作也必如徐铉所说:“及斯道之不行也,犹足以吟咏情性,黼藻其身”,由学白诗的“上以裨教化,舒之济万民”导向“下可理性情,卷之善一身”,向表现忧患意识或吏隐情趣全方面转化。白居易“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的感伤诗,尤其是后期所作的“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咏情性”的闲适诗和表现“亲朋合散之际”悲欢之情的杂律诗,也由此成为她们师学的关键对象。在诗之作用上较前期深入由实用
34、性转为心灵化,五代宗白诗前后期的这种转变和白氏一生前后期的转变轨迹有着惊人的相同。只因南唐宗白诗人毕竟重视元和古风,即使写作闲适一类诗也时和政事息息相关而并非一味沉醉享乐。宗白兼学李白,改变了前期宗白而往往兼学杜甫的作法。这种以李代杜所表现的宗白侧关键由外向到内向的转移,是后期宗白新变的主要标志。五代的宗白兼学李始肇于吴,然而南唐的承传却不只是江左诗歌的地方传统。诗学李白至南唐始盛,徐铉作诗“效李白体”,潘佑等亦学李白为诗,这最少有以下两大原因:一是南唐的道家思想较她国盛行,而唐代文学大家中道家思想突出的正是李白;一是南唐宗白诗人提倡师古,而李白不但提倡且尤以古体诗见长。其古风诗的“感伤己遭”
35、及“绮丽不足珍”、“雕虫丧天真”的文学看法,全部和南唐宗白诗人的反轻艳僻涩和取法白居易感伤诗相合,李诗不时表露的不求功名、自甘淡泊、重视气质的自我完善,也必定在主学白诗化烦扰为畅快自适、追求放怀自得的南唐诗人中引发普遍共鸣。所以,“我爱陶靖节,吏隐从弦歌”,便成了她们和李白、白居易师古的共同表现。不过南唐人更重取法汉魏古诗,甚至把抒写文人世俗情怀、生命意识以“深哀浅貌,短语长情”为特征的古诗十九首和诗经并举。也正因如此,后期诗人的宗白显著地改变了前期兼取温李、贾姚等沿袭晚唐的作法,也去除了前期以劝戒为主的僧偈作风。五代后期宗白诗的创新已不像前期那样基础限于部分方面的尝试,其自觉性和总体观照全部
36、显著地加强了,在力避温庭筠、贾岛诗之弊端的同时,对前期宗白诗的得失长短,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李建勋作诗直接汲取诗风分别靠近郑谷、王贞白的孙鲂、沈彬的创作经验,并和推重郑谷、王贞白进而追风李白、杜甫的孟宾于论诗唱和,且同受张籍诗影响。不过李建勋诗又和孟诗不一样,建勋诗风的个性特征是她入南唐后,在几经任相罢相的得意失意中才真正形成的,宦海浮沉致使其诗转为集中抒写性情,咏物吟怀自出肺腑。因她不甘为烦扰的政治纷争“耗真蠹魂”,其后半生半官半隐的生活、心境和白居易的“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极为相近,作诗每言“闲地”、“闲游”、“闲吟”、“闲愁”,大多不离一个“闲”字,现有不被信用近似屈赋的骚怨,更有放
37、怀自得,知足保和,却非沉醉于享乐,对花酒山水的依恋反应着对仕宦生涯的厌倦,所以其采菊、小园、溪斋、田家诸诗内容、情调又时近陶诗,文从字顺,清新淡雅。冯延巳、冯延鲁诗今虽不存一首,但延巳诗“识者谓有元和诗人气格”,就宋初王禹偁评延鲁诗所云:“词丽而不冶,气直而不讦,意远而不泥。有讽谕,有感伤,有闲适。范范焉,铿铿焉,真一家之作也”,可知其宗白既迥别于温庭筠、贾岛诗风,又克服了贯休诸人的缺点,多方面取法白诗并能独立成家。为时稍晚、影响更大的徐铉堪称五代后期宗白诗人的关键。徐铉作诗鄙弃“淫靡之态”,力争“高视前古”,“简练调畅”,走着不一样于“于苦调为高奇,以背俗为雅正”的创作道路。其诗也以此“具元
38、和风律”。她入宋后虽推重白居易诗的“主讽谏”,但她南唐时期所作诗300首,几乎全部抒写主观世界,属“讽谏”者可说没有,即使效白体所作长篇排律也少叙事而多言怀,从而把五代宗白诗的抒写个人真情实感推向极致,并集中到反应、揭示封建侍臣的生活情感上来。面对岌岌可危、风波翻覆的南唐政局,其为官吟诗更多循名尽职,“贵乎自适”。即使被贬后所作诗自许“迁客”、“贱子”,以屈、贾自况,也较李建勋诗少哀伤骚怨,以“自甘逐客纫兰佩”表明自保人格,并把陶渊明式的退隐闲居引入、扩展到上层官场之中,从而在“朝市”、“丘壑”间得乎“中道”上,表现出身居高官显位却缺乏从政热忱,视名位为身外之物、真情之累。因为徐锴、张洎、乔匡
39、舜、萧彧、钟茜、孙岘等一大批创作追求大致相同的诗人集结在徐铉周围频频唱酬,致使此种宗白新风大盛于南唐。经南唐众多诗人的相继探索,从而形成了五代后期宗白诗风的基础特征:吟咏性情。此期宗白诗极少反应社会现实,既少“刺”,又少“美”,咏史之作已不多见,就是抒写对现实的主观感受,较之前期也展现出范围的内敛和重心的转移,由表现广大士人怀才不遇之类的生活情感转为集中揭示上层官僚士大夫,尤其是高官显宦的值宿、从幸、侍宴、应制、赏花、歌酒等种种生活感受。其间因事动情、随感赋诗之作,时有今昔悲欢对比产生的“无主”之感和对国家、个人命运的忧患,却又一致表现出不漫渎君王,多自我宽慰以化解内心矛盾,并由仕进不能的隐退
40、转为仕宦无功的居闲。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五代后期宗白诗内容贫乏的致命弱点,但也为后世官宦文人宗白诗的写作别开新路。次韵唱酬。“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依韵唱和作为一个交际手段在五代前期虽已属习见现象,但唐末皮、陆以来,大力取法元白唱酬之举并成为诗坛风尚和宗白特征,至南唐才更为经典。以文雅著称的南唐二主作诗每要群臣和答,宴集则即席分题,次韵较胜,中主登楼赏雪和后主游宴北苑,君臣大规模唱和全部曾结为诗集,并由巨擘徐铉制序鼓吹。后主送弟从镒出镇宣州和钟茜外任饯别于石头城等,也堪称南唐群体唱和的诗坛盛事,其间恰多宗白诗人。至于徐铉,更是笔砚酬答略无虚日,其骑省集中作于江南的这类诗多至五分之三
41、以上,二徐和殷崇义等共咏庭梅,以长篇排律重复唱和,“频吟叹盛衰”。从诗大家“诗因此言志,我当分题”的自白可知,这类诗的关键写作动机仍属言怀,因此从中表现出的“以诗代书”的南唐宗白诗特征也较前愈加突出。虽说不无缺乏意境、韵味的应酬之作,却大多音调和美、词藻富赡,“相慰”“相娱”间也全部时有富于真情实感的佳篇,下启宋初君臣次韵应制唱和之风。“率意而成”。直抒胸襟而不刻意苦吟,是五代后期宗白诗改变了前期兼取温、李或贾、姚的作法,强调诗以言志,在“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的基础上形成的鲜明特征。南唐诗人才学较高,缘情致意,厚积薄发,上承元和体的“率意放辞”,现有所感,敏速成章,多用虚字,喜用白描,不但
42、其近体诗多流易畅达,因为追踪元和的江文蔚等“大长于古风诗”,此期出现的不少五言古诗也质朴自然,还颇受李白“语多率然而成”的影响,写法上取得更大自由。五代后期宗白诗并非不议论说理,只是改变了前期贯休、杜荀鹤诸人古近体诗据理说教的议论方法,偏重师学张籍的寓说理于描绘,进而探索理致论议和情景爱好相结合的更佳创作路径,在触物兴怀之下用含有形象美的语言描绘个人的体验、感受,以隐喻表示思理,虽仍属“直而不迂”,却能效学张籍诗的“思深而语精”,获取“连类近而及物远”、“取譬小而其旨大”的艺术效果,有利抒发君臣内心不得不言而又不便直言的难言苦衷。清淡典雅。后期宗白诗风的这一主格堪称对前期粗疏俚俗的反拨。中唐以
43、来的诗之俗浅经五代前期的极端化,已成为诗歌不可逆转的必定走势,南唐人的学白杂律即其表现之一。不过和南唐君臣在绘画、书法、音乐等很多艺术门类中的追求淡雅相一致,其宗白作诗通常已不再下偶俗好,渐重“以俗为雅”,或用事典、语典咏俗物,或化俗字俚语为精金,以“思深语精”矫粗浅乏味,从而把前期偏离白氏士大夫之俗的走向重新拉回到原来的轨道,并进而形成雅俗参融的特征。徐铉等作为“经史百家烂然于胸中”的大学问家,每“资学认为诗”,却“学深而不僻”,并改变了前期变风变雅的风调而归之中和。李昉称徐铉文笔“有雅正之体”,差可移为南唐宗白诗风的总评。个性鲜明的南唐宗白诗风,其势力之强大甚至制约了江左追风贾、姚的李中诸
44、人的诗歌创作,使其继齐己以后深入趋近白居易。而其风北渐,更有力促成了中朝宗白诗风的兴盛。中原五朝诗至迟在后唐时已经有冯道主讽谏、好说理,并以多用俚语和罗隐、杜荀鹤并称,推崇白居易的秦王李从荣还结集了高辇、何仲举等多人唱和,曾入其幕的齐己有“元白终存作者来”语,南唐江文蔚也出自从荣幕府。不过至南唐开国,经南风北渐和后周政经、文化的全方面振作,中原宗白诗风才日益盛行。和南唐孟宾于遥相唱和的李昉,“诗务浅切,效白乐天体”;冯延鲁入汴三年,“和中朝卿大夫以诗酒自乐,篇咏间发,传于人口”;杨徽之由江左入后周投窦仪、王朴,“深赏遇之”。经周世宗及群臣的提倡,南北相继兴盛、愈演愈烈的五代宗白诗风以强劲势头进
45、入北宋。五代十国的诗歌流变对宋初诗坛产生了巨大作用。然而以往的论者却忽略这一基础史实,以宋初的“白体”诗上接唐代的“元白”派。如此论诗,极难正确把握宋初诗歌的个性特征并深入认识宋初诗坛的很多现象。实际上,宋初诗人虽喜标举中晚唐名家,但她们从未超越五代而把中晚唐诗作为学步的起点。宋初诗人推尊白居易,而直接师学的却是五代入宋的宗白大家徐铉、李昉;田锡、张咏等还学韦庄、郑谷、贯休为诗。正因她们承传经五代人演变了的白氏诗风,故称“白体”而不称“元白体”是有其道理的。宋初王禹偁的宗白兼学杜甫,直接收到徐铉高徒郑文宝的启示,实属五代前期韦庄诸人宗白兼学杜甫的回归和发展。五代不一样诗风实力大小的对比,决定了在宋初诗坛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宗白诗风,而不可能是追风温、李的艳诗。所以能够说,不探讨五代十国的诗歌流变,最少宋初诗的研究是极难深入的。作者介绍:贺中复,1937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 温馨提示:
1: 本站所有资源如无特殊说明,都需要本地电脑安装OFFICE2007和PDF阅读器。图纸软件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压缩文件请下载最新的WinRAR软件解压。
2: 本站的文档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图纸等,如果需要附件,请联系上传者。文件的所有权益归上传用户所有。
3.本站RAR压缩包中若带图纸,网页内容里面会有图纸预览,若没有图纸预览就没有图纸。
4. 未经权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将文件中的内容挪作商业或盈利用途。
5. 装配图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保护处理,对用户上传分享的文档内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编辑,并不能对任何下载内容负责。
6. 下载文件中如有侵权或不适当内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立即纠正。
7. 本站不保证下载资源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时也不承担用户因使用这些下载资源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