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M
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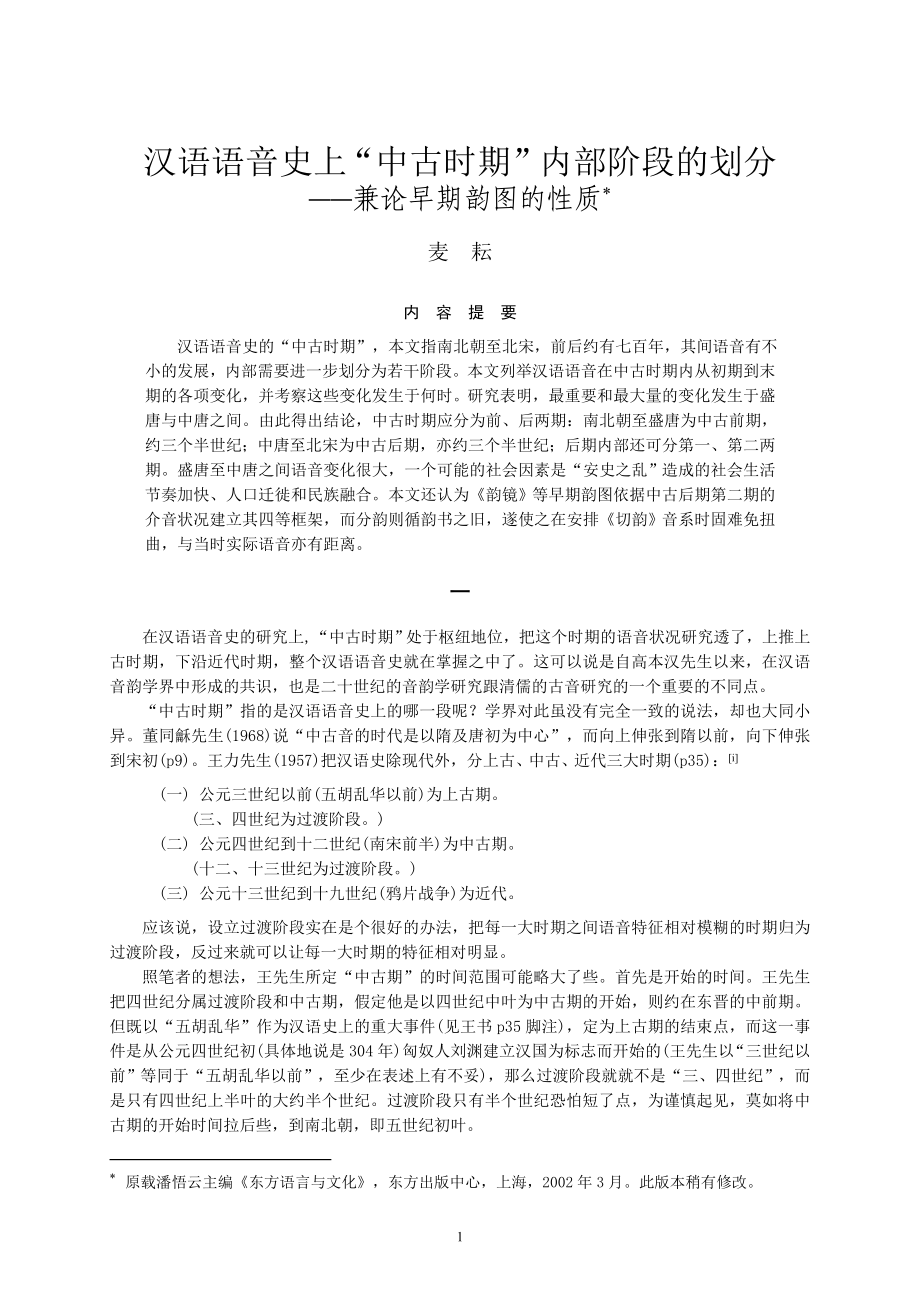


《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M》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M(10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兼论早期韵图的性质* 原载潘悟云主编东方语言与文化,东方出版中心,上海,2002年3月。此版本稍有修改。麦 耘内 容 提 要 汉语语音史的“中古时期”,本文指南北朝至北宋,前后约有七百年,其间语音有不小的发展,内部需要进一步划分为若干阶段。本文列举汉语语音在中古时期内从初期到末期的各项变化,并考察这些变化发生于何时。研究表明,最重要和最大量的变化发生于盛唐与中唐之间。由此得出结论,中古时期应分为前、后两期:南北朝至盛唐为中古前期,约三个半世纪;中唐至北宋为中古后期,亦约三个半世纪;后期内部还可分第一、第二两期。盛唐至中唐之间语音变化很大,一个可能的社会因素
2、是“安史之乱”造成的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口迁徙和民族融合。本文还认为韵镜等早期韵图依据中古后期第二期的介音状况建立其四等框架,而分韵则循韵书之旧,遂使之在安排切韵音系时固难免扭曲,与当时实际语音亦有距离。一在汉语语音史的研究上,“中古时期”处于枢纽地位,把这个时期的语音状况研究透了,上推上古时期,下沿近代时期,整个汉语语音史就在掌握之中了。这可以说是自高本汉先生以来,在汉语音韵学界中形成的共识,也是二十世纪的音韵学研究跟清儒的古音研究的一个重要的不同点。“中古时期”指的是汉语语音史上的哪一段呢?学界对此虽没有完全一致的说法,却也大同小异。董同龢先生(1968)说“中古音的时代是以隋及唐初为中心
3、”,而向上伸张到隋以前,向下伸张到宋初(p9)。王力先生(1957)把汉语史除现代外,分上古、中古、近代三大时期(p35): 准确地说,这是汉语语音史的分期,词汇、语法史的分法容有不同。汉语语音、词汇、语法的历史分期如何统一,是个需要另外研究的问题。 (一) 公元三世纪以前(五胡乱华以前)为上古期。 (三、四世纪为过渡阶段。) (二) 公元四世纪到十二世纪(南宋前半)为中古期。 (十二、十三世纪为过渡阶段。) (三) 公元十三世纪到十九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应该说,设立过渡阶段实在是个很好的办法,把每一大时期之间语音特征相对模糊的时期归为过渡阶段,反过来就可以让每一大时期的特征相对明显。照笔
4、者的想法,王先生所定“中古期”的时间范围可能略大了些。首先是开始的时间。王先生把四世纪分属过渡阶段和中古期,假定他是以四世纪中叶为中古期的开始,则约在东晋的中前期。但既以“五胡乱华”作为汉语史上的重大事件(见王书p35脚注),定为上古期的结束点,而这一事件是从公元四世纪初(具体地说是304年)匈奴人刘渊建立汉国为标志而开始的(王先生以“三世纪以前”等同于“五胡乱华以前”,至少在表述上有不妥),那么过渡阶段就就不是“三、四世纪”,而是只有四世纪上半叶的大约半个世纪。过渡阶段只有半个世纪恐怕短了点,为谨慎起见,莫如将中古期的开始时间拉后些,到南北朝,即五世纪初叶。其次是结束的时间。王先生把上古期的
5、结束同“五胡乱华”造成的国家崩溃(准确地说是政权的更迭和分裂)、部族(民族)融合和人口迁徙联系起来,是非常有眼光的。那么中古期的结束是否也可以同当时的战乱事件相联系呢?可以的,那就是金人的入侵、北宋的覆灭。宋室南渡与晋室南渡的相似本来就很容易让人引起联想。这不是本文的主要论题,不拟在此详细探讨。现在暂且把中古时期的结束、中古到近代过渡阶段的开始定在北宋与南宋之间,即十二世纪初叶。如此,本文所指的“中古时期”就是从南北朝到北宋,用公元纪年,是从五世纪初叶到十二世纪初叶,大约有七百年。二 周祖谟先生(1963)指出,切韵(601)代表“六世纪文学语言的语音系统”。笔者极为推崇此说。尽管有的学者认为
6、切韵不是单一音系、不是自然的音系,但至少都承认它是中古音研究中最为重要的、无可替代的参照系。不管用任何其他资料来构拟中古音,都不可能撇开切韵的框架来进行。从这个意义上说,切韵是公认的中古音的代表。当然,即使切韵确实反映六世纪前后的某一种语音系统,它也一定不能与十一、十二世纪的任何一种音系相吻合,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一个语音系统经过数百年的时间,就算没有剧烈变化,也不可能保持原样,这是常识。所以,中古时期内部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也已成为学界的共识。不过,对中古时期内部如何划分,却还是见仁见智。下面列举几家的说法,并略加评论。(一) 王力先生(1985)卷上第三章是“魏晋南北朝音系(22058
7、1)”,第四章是“隋中唐音系(581836)”,第五章是“晚唐五代音系(836960)”,第六章是“宋代音系(9601279)”。这是把与中古有关的时期分作了四段。王先生放弃了他早年的观点。第一,魏晋南北朝合为一段,“五胡乱华”在汉语语音发展上再也不算是个关键了;第二,南宋时期也不再有一个向近代过渡的阶段。不过笔者觉得在这两点上,还是他原来的说法较胜。关于第一点,“五胡乱华”且不说它。王先生建立魏晋南北朝韵部时,全用南北朝人的押韵材料,但没说明这些材料为什么可以同时代表魏晋音。魏晋和南北朝该不该合为一段,还有待证明。另一方面,王先生在讨论隋中唐音系时,用了陆德明经典释文的反切材料。此书成于隋朝
8、已建立、南朝的陈朝尚未结束的公元583年,说它的注音是代表隋音还是代表南北朝音(至少是南北朝后期音)都是可以的。在南北朝跟隋之间划开,未见其宜。在第二点上,王先生纯用从南宋朱熹(1130-1200)的“叶音”中整理出来的材料来证明宋代音。这些材料略嫌单薄不说,它们能否代表北宋音,还得打个问号。更重要的是对唐代的切分。对隋中唐音系,王先生用经典释文和初唐的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对晚唐五代音,则用五代朱翱的反切。它们自然代表了不同时代的音系,不过为什么要把两段的分界划在中唐与晚唐之间?为什么不是早一些,譬如在初唐与盛唐之间,或盛唐与中唐之间,又不是晚一些,譬如在晚唐与五代之间?王先生没有解释。(二)
9、 陈振寰先生(1986)第五章是“隋唐音系”,第六章是“等韵学说与五代宋音系”。这是分两段(“两汉魏晋南北朝”统归上古到隋唐的过渡期)。陈先生以切韵代表隋唐音、以韵图代表五代宋音,他说:“韵图的框架就是韵图当时实际语音面貌的反映。一切看来与韵书不同之点都是唐末到两宋实际语音发展的结果。”(p245) 对这一观点,笔者从原则上说非常赞同(关于韵图的性质,下文会讨论到)。不过,把两段的分界划在唐与五代之间是否最合适,还可以讨论,讨论的焦点是:形成韵图音系的最重要和最大量的变化发生于何时?其实这也正是本文写作的主要目的。(三) 竺家宁先生(1991)第十讲“中古语音系统”以切韵音为狭义的中古音,包括
10、魏晋六朝隋唐,又称为“中古前期”(p290),第十二讲“中古后期语音概述”则是讲宋代音。这也是分两段。这里列举的几家说法中,只有竺先生还使用“中古音”的概念,并明确地在中古内部分“中古前期”和“中古后期”。对此笔者深为佩服。反观像王力先生(1995)那样,把从先秦到明清分九段之多,跟中古时期有关的就分四段,而每段并列,显得过于细碎,且有类流水帐。笔者还是主张在第一层次上分三大时期,每一时期之间可以有过渡阶段;而每一时期内部,在第二层次上再分阶段(如竺先生这样分前期、后期之类);如有必要,还可在第三层次上再分小段。从科学学上说,有层次的分类才是科学的分类。不过,仅凭“隋代的切韵到了唐代仍然十分风
11、行”(p290),未必就能把整个唐代囊括到中古前期去。此外,竺先生书的第十二讲所介绍的几种材料中,有些性质上相去甚远。如集韵分韵与广韵全同,其中所增收的一些来自早期“音义”著作的字音还带有切韵前的语音遗迹,同时在反切用字上和某些字音上又受宋时语音的影响,可说是个以切韵音系为主料的大杂烩;而古今韵会举要成于宋末元初,其按“平水韵”分韵是极传统的做法,可置不论,而其“字母韵”系统则源自蒙古字韵,与后出二三十年、作为近代音代表的中原音韵也相当接近。这就涉及如何对“中古后期语音”进行定位的问题。 (四) 黄笑山先生(1995)分三段(pp4-8):切韵(盛唐以前) 一段、中唐至五代一段、两宋一段。黄先
12、生把切韵后演变的起始点定在中唐,是凭借了坚实的证据的:中唐慧琳的一切经音义、中唐时的梵汉对音、中唐以后的韵文材料等。相比之下,书中对五代到宋的变化就没怎么说。不过这本不是黄书论述的重点,所以无可指摘。黄先生认为各段之间改变的关键在于标准语基础方言的转移:切韵是伊洛之音,中唐五代是“唐京雅音”即长安音,宋代又是汴洛音。中唐五代标准语为长安音的论据,是慧琳等人贬斥切韵为“吴音”,而标举“秦音”。不过晚唐李涪刊误认为“凡中华音切,莫过东都,盖居天下之中,禀气特正”,推崇洛阳音,也同样痛诋切韵为“吴音”。可见慧琳等人提倡“秦音”并非针对“伊洛之音”,因为此时的洛阳音同样也已变化,而且变化的方向跟长安音
13、应是一致的。洛阳音跟长安音本来就没有太大区别,特别是在音类上。笔者认为,中唐以后长安音的地位提高是事实,但与此同时,洛阳音被视为正音的传统未必就失去了。所以,照笔者看来,中唐以后的语音演变,固不排除地域的因素,而更多的还是由于时代的关系。 储泰松先生(2001)认为,唐代佛教典籍所谓“秦音”并不是专指长安一带的关中音,而是是北方通语。如此说成立,则黄先生的说法就要重新考虑。三为了更精确地考定中古时期内部各阶段的划分,现在采取这种办法:看从中古时期之初到中古时期之末总共发生了多少项变化,再逐项观察它们各自发生的时间。首先,确定切韵音系为中古初期的代表音系,辅以其他资料。王力先生(1936)在考察
14、了南北朝诗人用韵后认为:“切韵大致仍以南北朝的实际语音为标准。”这是指韵母系统。切韵的声母和声调基本上能够代表中古初期的“雅音”,就更没什么问题。 其次,中古末期音可以拿切韵指掌图来代表,再辅以其他资料。指掌图伪托于北宋司马光,南宋人董南一已信以为真,大约撰作年代在北宋末或南宋初(参看李新魁先生1983:p184),中古时期的演变内容基本上都汇集其中了。下面分声母、韵母、声调逐一列举汉语语音在中古时期内的变化,并考察它们发生于何时。有一个问题要先说一说:据周祖谟先生(1963),切韵折衷于南(金陵)北(邺下 用颜氏家训音辞说则为“洛下”。从语音上说,邺下与洛下实际上应无二致。)之间,例如鱼、虞
15、韵南分北不分(此处的“北”实际上限于河洛音,而长安音是分的),切韵从南,指掌图鱼、虞为一,这样就不能问“鱼虞何时合流?”而应当问“在鱼虞分合方面,雅音何时从北?”限于篇幅,对大部分问题不能在此详细论证,有关资料请看文后所附参考文献。一、声母方面 (1) 轻唇化。潘悟云先生(1983)指出,轻唇化分两个阶段:一是“非、敷、奉、微”与“帮、滂、並、明”分开,唇齿塞音从双唇塞音中分化出来,即p pf ,ph pfh等;二是“非、敷”合流,从唇齿塞音变为唇齿擦音,pf和pfh都变成f 。潘先生考证第一阶段发生于八世纪中叶(中唐),第二阶段发生于九世纪中叶(晚唐)以后 初唐玄奘的梵汉对音中轻重唇的读音有
16、区别(施向东先生1983)。笔者认为,轻重唇音读音的分化在玄奘时代已经开始,但尚未形成音位上的轻重唇对立。 (2) 庄、章组合一。切韵两组分别极严,整个唐代都未见混淆。唯唐末守温韵学残卷两组合为一组,北宋邵雍(1011-1077)皇极经世书声音倡和图也作一组。五代朱翱为说文系传作的反切中,浊音崇与常、船相混,清音庄与章、初与昌、山与书有少数混。 这两组在元代声母一样而韵母不同:庄组不带i而章组带i 。两组声母合并的先决条件是庄组三等韵的i消变,章组再变同庄组,形成一条“拉链”:ti- ti- t- 。韵图形制的基础之一是把庄、章两组作为一组,摆在同一栏,庄组列二等而章组列三等。两组如不合流,就
17、不可能有韵图。守温时韵图形制应已成立,他把两组合一是可信的,其时庄组声母已不带i 。那么为什么朱翱反切中两组分多混少,且庄组反切下字仍常用三等韵字呢?笔者以为可以这样解释:一,当庄组ti- t- 之变已发生,而章组尚未ti- ti- 之时,两组形成互补分布,从音位上说已可以视为一组,但发音上还有差距,成为互为反切上字的障碍。二,庄组声母后的i脱落与否处于两可阶段,即“词汇扩散论”所谓“共时变异”阶段(参王士元先生1979)。 这一段所说的i介音实际上包括了后面提到的i和 I 两种。 (3) 喻三与喻四合流。切韵此二母有别,一般认为喻三是匣母的细音。中唐慧琳一切经音义(810)中两者仍泾渭分明。
18、罗常培先生(1933)根据藏汉对音指出唐五代(这里的“唐”实际上指中唐以后)西北方音中此二母相混。产生于唐末的早期韵图已形成统一的喻母。邵雍书亦将喻三和喻四字列为同一个“音”(声母)。(4) 日母擦化。日母本是纯鼻音,后来变鼻擦音。这可从梵汉对音看得出来。初唐玄奘(600-664)用日母字译梵文 (),盛唐不空(705-774)则用日母字兼译 和j ( d ),可见有 之变。再往后,日母随章组一道翘舌化为 。这只是读音变化,不涉及音位调整,所以从指掌图中看不到。 (5) 知组的演化。王力先生(1985)认为隋代和初唐时知组尚未从端组中分化出来,知组之成立见于盛唐何超晋书音义(747以前)。不过
19、这个观点还有待进一步证实。到北宋,邵雍书将知组次照组后,周祖谟先生(1943)认为已开始塞擦化。指掌图也有几处知、照组字误置。不过似乎仍未有充分证据证明北宋时两组已合并,这样,知组塞擦化就仅是读音变化,而未上升为音位变化。 (5) 全浊声母分化。邵雍书以平声配次清、仄声配全清,开后代分化之先。黄笑山先生(1994和1995)考证全浊声母从中唐开始变为“清音浊流”;麦耘(1998)在此基础上,认为邵雍时仄声的“浊流”变弱,近似全清。不过,只要这些声母未真正清化,未分别并入清声母中,其音位关系就仍跟在切韵中是一样的。因此,指掌图不反映这一变化也是自然的。 (6) 常、船母相混。金陵音一直是如此,而
20、洛阳、长安音在中古初期能区分,后来也混淆了。初唐洛阳人玄奘的梵汉对音、玄应一切经音义(大约可代表长安音) 、盛唐洛阳人何超晋书音义反切是能区分的;中唐慧琳一切经音义(810,用“秦音”即长安音)则相混。假定在这点上洛阳与长安同时发展,则变化发生于盛唐到中唐之间。韵图两母分列,但位置颠倒(参陆志韦1947),其实已不能区分。 二、韵母方面 (1) 三、四等韵合流。切韵三等韵基本上自有一套反切上字,而四等韵与一、二等韵用同一套反切上字,显示三等韵有前腭介音而四等韵没有。初唐玄应音、盛唐何超音均同切韵。而中唐慧琳音三、四等韵用一套反切上字,与一、二等反切上字有别,说明四等韵产生了前腭介音,与三等韵合
21、流了(实际上是与三等韵中的i介音字合流,见后文所述)。三、四等韵合流是韵图体例赖以建立的最重要的基础,是韵图介音系统同切韵介音系统最重大的区别。这一变化发生于盛唐到中唐之间。 (2) 一、二等重韵合并。据王力先生(1936),在南北朝诗人的用韵中,除庚二耕同用外,所有一、二等重韵都有区别(按:押韵同用不等于混合,不同用则肯定有别),而第三期(六世纪上、中叶以后)山韵似归删韵。隋代韵文中,庚二耕、删山之间还略有区别,东一与冬、咍与泰开、灰与泰合就肯定不混(蟹摄二等和咸摄因字少不能定)。玄应音庚二耕、删山、东一冬、衔咸合并;何超音更是皆夬、咍泰开、灰泰合、覃谈合并。一、二等重韵合并是在初唐和盛唐期
22、间(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逐步实现的 佳韵自初唐始即摇摆于皆与麻之间,是有方言之别。其韵中字或与皆、或与麻合并亦应出现较早,惟其中线索当作专文探讨。 (3) 三等重韵合并。A. 止摄。在隋代韵文中,支、脂、之、微4韵分立。玄应音脂之合并,何超音支开也合进来(但支合仍独立),到慧琳音4韵合一。B. 蟹摄。玄应祭、废不混,慧琳合一。C. 遇摄。玄应、慧琳鱼虞不混。朱翱合一。晚唐墓志铭押韵中的鱼、虞已不辨。D. 流摄。颜师古(581-645)汉书音注尤、幽两韵界限清楚,慧琳两韵合一。E. 梗摄。玄应庚三与清有别,慧琳音合流。在唐代墓志铭用韵中,初、盛唐这两韵不混,中、晚唐合流。F. 通摄。玄应东三与
23、钟分立,慧琳则唇音混,其他声母分。朱翱完全合流。唐代墓志铭押韵显示,从初唐到晚唐,东三与钟都是有区别的。G. 臻摄。玄应、何超真与欣都不混,慧琳音亦约略能分(部分真韵重纽三等字进入欣韵)。朱翱两韵混。晚唐墓志铭押韵中,文与谆尚有别;欣韵字少,难以判断。现在假定它跟文平行,则臻摄三等重韵合流的时间在五代。H. 咸摄。玄应、何超严凡不分,而盐韵独立。按切韵严凡基本互补,它们可能本就没区别。慧琳音此3韵合一(凡韵唇音字见后)。 三等重韵的情况较复杂。陆德明真、欣相混,是金陵音的特点,不论。何超鱼、虞无别,则为洛阳音特点,亦不论。玄应、何超尤幽合一,不过初、盛唐轻重唇音尚未分化,此两韵如合流,后来的分
24、化条件就找不到了。此存疑。另,东一与冬、东三与钟在切韵是平行的,但重韵合并的时间有先后。 (4) 江、宕两摄合流。江摄原较接近通摄。隋代用韵江已接近宕。从唐代墓志铭用韵看,江摄在初唐时摇摆于通、宕两摄之间,盛唐时接近宕摄。不过朱翱反切江、宕未混,可能元音还略有不同。北宋时两摄不分。 (5) 梗、曾两摄合流。唐代墓志铭用韵表明,此二摄的入声韵在中唐合流(不过在慧琳反切中没表现)。它们的舒声韵合流则要迟至北宋。 (6) 止摄与蟹摄部分字合流。包括两方面:A. 蟹摄三、四等韵与止摄合流;B. 蟹摄一等合口字与止摄合口字合流。朱翱反切在这两方面都略有表现。从邵雍书中可见到A;在北宋中原韵辙中,A已完成
25、,B还处在变化过程中。指掌图两者都完成了。可以说这变化开始于五代,完成于北宋。 (7) 韵母出现。包括两方面:A. 止摄精组字读 ;B. 止摄庄组字读 。指掌图止摄精组字列一等,第一次明确表示这些字读 。不过据王力先生(1982),在朱翱反切中已有此韵母。由于蟹摄三、四等韵的精组字不变为 ,所以这一变化应发生于蟹摄三、四等韵与止摄合流之前。在元初蒙古字韵中,止摄庄组字读 而章组字尚未有此变化,这说明 的产生应在庄、章组声母合并之前。就是说, 韵母至少在唐末五代已出现。 从切韵指掌图可看到 ,但看不到 。由于蟹摄三四等韵并入止摄,其精组字占据了四等位置,止摄精组字不得不列入一等,便显出了 ;蟹摄
26、三等无庄组字,止摄庄组字没有位置冲突的问题,所以没作特殊处理, 就没显出来。这并不能说明切韵指掌图没有 。相反,韵图把这些字列于二等,倒是暗示它们已不是i了。(8) 侯、尤韵系唇音变入遇摄。慧琳反切中部分侯、尤韵唇音归遇摄。唐代墓志铭用韵显示侯韵唇音字从盛唐开始与遇摄字相押,中唐基本归入遇摄;尤韵唇音从中唐开始转向遇摄。北宋词韵显示,其时尤韵唇音尚有个别字未最后完成变化。 (9) 轻唇音声母后的前腭介音脱落。慧琳反切凡韵唇音有读为二等者,元韵唇音有读一等或二等者,东三唇音有读一等者。这说明自中唐始,轻唇音声母后的前腭介音逐步脱落。到北宋邵雍的书中,轻唇音除还跟单韵母i相拼外,后面再不带前腭介音
27、了。 (10) 江、宕摄入声韵读效摄音。邵雍书开始有此现象,指掌图更明显。 (11) 元韵系转向山摄。中古初期元韵系与魂韵系关系密切,指掌图在山摄,与仙韵系合流。笔者认为元韵近魂是南音(金陵),而在北音(洛阳、长安)是读同仙。玄应虽在北,但元韵不与仙同,可见仍以南音为正。慧琳摒弃所谓“吴音”,元韵与仙韵(重纽三等)合一。显然此时的标准音已经以北音为正了。在初、盛唐墓志铭用韵中,元韵与臻摄(主要是魂韵)关系密切,到中、晚唐就与山摄字(主要是仙、先韵)关系更密切。 (12) 从朝鲜汉字音、汉越语和集韵的反切用字看,中古时期已有二等韵字带i (或音质相近的)介音的迹象,但发生的年代不能肯定。 三、声
28、调方面 (1) 浊上变去。慧琳音中有一部分全浊声母上声字读作去声。其他资料也可证明这一变化从中唐已经开始。(2) 入声韵尾消变。晚唐墓志铭用韵中,臻摄入声韵与梗、曾摄入声韵合为一部,可见-t尾与-k尾的相混已开始。邵雍把原-t, -k尾字都配阴声韵而不配阳声韵,可见它们已转化为-/ 尾 (惟-p尾未变)。四根据上述材料,可以排一个中古各时期出现语音变化的清单,自南北朝以降,依次是:隋、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凡见于唐末的变化算在五代)、北宋。所标的年代只具有参考价值,理由不言自明。(一) 隋(589年开始)。江摄开始转向宕摄。 (二) 初唐(618年开始)。庚二耕、删山、东一冬、衔咸、脂
29、之合并。 (三) 盛唐(713年开始)。日母擦化;皆夬、咍泰开、灰泰合、覃谈合并;支开与脂之合并;侯韵唇音开始转向遇摄。此外,知组可能于此时独立。 (四) 中唐(766年开始)。轻唇音分化;常、船母相混;全浊声母变“清音浊流”;三、四等韵合流;止摄4韵全部合流;庚三与清、严凡与盐合并;梗、曾摄入声韵合流(至少是非常接近);尤韵唇音开始转向遇摄;轻唇音声母后的前腭介音开始脱落;元韵转向山摄;浊上变去开始发生。此外,尤幽合并可能发生在中唐,但有可疑之处,祭废合并是盛唐还是中唐的事也不能定。这两项涉及面很小,无大碍。 (五) 晚唐(839年开始)。非敷相并;喻母成立;鱼虞合流;-t与 -k尾开始合并
30、。 (六) 五代(907年开始。如包括唐末,则此一时期的开端可往前推一些)。庄、章组合流;东三与钟、真谆与欣文合流;止摄与蟹摄部分字接近; 韵母出现。 (七) 北宋(960年开始)。知组出现擦化迹象;全浊声母有分化为两类的倾向;江、宕两摄合流;梗、曾两摄的舒声韵合流;止摄与蟹摄部分字合流;江、宕摄的入声韵出现效摄读音;轻唇音中的i介音基本消亡;-t, -k尾变为 -/ 尾。暂时把二等韵开始出现i介音算在这里。从数量上看,自中唐开始出现的语音变化项目最多,或者说,从盛唐到中唐之间发生的变化最为大量。从质量上看,在上述所有发展中,最为重要的是两项:庄、章组声母合一和三、四等韵合流,其中以后者尤为关
31、键(关于这一点,下文会论及),而这正是从中唐开始的。就是说,最重要和最大量的变化发生在盛唐与中唐之间,因此应从这里把中古时期划分开来。其他时期是否也可以划开呢?中唐以前,主要是某些重韵的合并,尽管造成了韵母系统的简化,但大框架没动,跟盛唐到中唐的变化不能相比。唐末五代的庄、章合流是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其重要性可与三、四等韵合流相提并论,不过这时期的变化从数量上说不多。北宋的演变略多,惟重要性稍逊。笔者的意见,可在唐末五代作第二层次的阶段划分。总括来说,汉语语音史的中古时期可以从盛唐与中唐之间划分为两期:南北朝到盛唐为中古前期,约三个半世纪;中唐到北宋为中古后期,亦约三个半世纪。中古后期还可以再分
32、:唐末以前为后期的第一期,为时一个世纪出头;此后为后期的第二期,有两个多世纪。前面说过,战乱常常能影响语言出现重大发展。在中古前、后期之间,发生了一场持续时间不长但规模很大、对当时社会的冲击也很大的战乱“安史之乱”(755-763)。这一事件不仅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实际上也是中国封建社会从顶峰向下滑落的起点。在长期太平盛世之后突如其来的战乱造成了社会生活节奏的骤然加快,以逃难形式出现的人口迁徙不必说了,少数民族对战争的积极参与(战争双方都有大量的少数民族军队)大大促进了民族融合。这些都会是造成语言加速变化的社会因素。至于中古后期的第一、二期之间,也是战乱频频:先是王仙芝、黄巢起义(874
33、-884),此后直至唐朝灭亡,军阀争战不曾中断过。第二期的最初一段(五代)中国北部也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中。从前面列举的资料看,五代到北宋之间,语音的变化也不小。可以认为第二期的中段以后(北宋,960-1125)是相对稳定的时期。五 高本汉先生(1915-1926)在构拟切韵音系时,非常倚重从韵图中获得的信息。这本来无可非议。问题是他低估了(虽然不是完全忽视了)韵图与切韵在音系上的差异。例如他认为韵图三等的声母是j化的,一二四等的声母是不j化的。可是切韵三等韵中的重纽两类字用的是同一组反切上字,而在韵图它们分列三、四等。“重纽四等”的存在不但使高氏的“三等声母j化说”站不住脚,也直接动摇了他的“三
34、等韵带辅音性i 介音,四等韵带元音性i介音”的拟音体系。 在跟韵图与切韵的“等”有关的术语中,最流行的两个是“假二等”和“假四等” 这两个术语最早出于日本的中国语学界。承平山久雄先生赐告,“假”并非“真假”之“假”,而是“假借”之“假”,是借用二等和四等位置的意思。既认为韵图直接反映切韵音系,则切韵一、二、三、四等韵分别列韵图一、二、三、四等就是天经地义的;惟“本应”列在三等的三等韵庄、精组之安排到二、四等,只因韵图不合只为齿音声母安排一栏地位;此外,韵图只立一个喻母也使两个喻母中的一个(喻四)不得不挤到四等去了。此即所谓“假”。其实还有常遭遗忘的重纽四等,也该算是“本应”列三等而却列入四等的
35、“假四等”。为解释韵图与切韵系韵书的龃龉,古人制定了许多“门法”,后为元人刘鉴归纳为十三门法,其中就有七项是跟“假二等”、“假四等”(含重纽四等)有关的(参看李新魁先生1980)。难怪后来不少学者指摘韵图和门法:造韵图时体制不善,复以门法来加以弥补,真是徒乱人意。其实这些学者是不了解以下事实:在韵图产生的时代,语音已不同于中古前期的切韵,要完全按切韵的系统来编韵图,既不可能,也没必要。说不可能,是因为唐末或宋代人对切韵系统上的理解,当还比不上今天的语音史家;说没必要,则涉及韵图的功用:当时的人们编韵图不是为了研究切韵音系,只是为了拼读韵书中的反切(参看赖江基先生1991)。所以韵图是以中古后期
36、之第二期的语音为基础来编制的,它与切韵(广韵) 之间的扞格之处,往往暗示着数百年间语音的变化。至于门法缕列早期韵书的反切与韵图列字的矛盾,大部分只要改变一下叙述的角度,实质上就可以理解为对中古前期与中古后期语音差别的陈述。 有一点亟须讲清:韵图自来即有“等”的概念(现见最早的是唐末守温韵学残卷里的“四等轻重例”),而切韵中本无“等韵”的概念,只是现代的学者把切韵与韵图结合起来研究,遂取韵图“等”的概念略加改造,用于切韵音系的。如果现在反过来说,韵图的“等”本应与切韵的“等韵”一一对应,凡有不对应之处即为韵图体制的缺陷,那就是本末倒置了。现在分切韵、韵图两方面来谈。切韵这一面,放弃了j化说,便可
37、根据切韵反切上字的分组情况,认定中古前期一二四等韵无前腭介音,而三等韵有前腭介音(参陆志韦先生1947和李荣先生1953)。三等韵介音实又分两种。俞敏先生(1984)据梵汉对音,指出重纽三等带r介音 (按:当为含卷舌音色、相对模糊或松弛的i介音,可暂依陆志韦先生写作 i ),重纽四等带y (等于j或i ) 介音。依切韵反切下字的统计 (见麦耘1988和1992),三等韵精组、喻四、章组、日母与重纽四等同类,是带i介音。另一方面,梵汉对音的资料证明庄、知组是卷舌音,则它们自然带有跟重纽三等一样的含卷舌音色的i 介音(来母跟知组同类)。喻三介音也与重纽三等相同(以下把切韵带i介音的称“三等韵A类”
38、,带i 介音的称“三等韵B类”)。此外,切韵二等韵有一种独特的、含卷舌色彩的后腭介音,此处不能详论(参看许宝华、潘悟云先生1994、麦耘1992)。在韵图这一面,可以切韵指掌图为中古末期韵图的代表,它基本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语音。如果说早期韵图如韵镜因齿音只有一栏,还可以让人说“庄、精组假借二、四等”的话,指掌图就没这个问题,因为它是把声母一字儿排开的。切韵庄、章两组在此不分列,只作一组(照组),可见庄组的前腭介音确已消失,否则近代庄、章组字不同音就成为不可能,所以庄组之置于二等绝非“假”。 切韵指掌图照、精两组分栏以后,精组仍列在四等,而宁愿让三等位置空着,这又是“假四等”之说无法解释的
39、。切韵四等韵在韵图列于四等,显示带i介音,如前所述,是盛唐至中唐之间变化的结果。四等韵不是一般地与三等韵混,而是只与三等韵A类混,不与三等韵B类混,又说明三等韵两类一直是有差别的 直至元初蒙古字韵尚可见这种差别的残余,而且总是四等韵与重纽四等为一类,纯三等韵与重纽三等为一类(参看麦耘1995b)。重纽两类在梵汉对音中r与y的差别,到宋代看不到了,这可能是重纽三等介音中的卷舌成分消失了,与重纽四等介音只有松紧之别,梵汉对音表现不出来了。例如四等韵先韵与三等韵仙韵的重纽四等和精组相混,而与重纽三等有别,与仙韵的来母也不混;仙韵的重纽三等就与“纯三等韵”(属于三等韵B类) 元韵相混。类似的现象在慧琳
40、音中已能看到:仙韵A类与先韵混,B类与元韵混。慧琳音与指掌图不同的是:后者仙韵章组和日母列在三等,与元韵同列;而前者仙韵章组和日母基本上为A类,与先韵为一类,只有个别字转入B类。这很好理解:指掌图的章组和日母是卷舌音,介音受声母影响而变松,成为i;而中唐时章组和日母还是舌面音,介音当然还是i 。从慧琳音反观指掌图,亦可信指掌图所反映的语音状况的真实性。现在我们看到,所谓“假四等”倒是在切韵时代就具有了韵图四等的特征,即带有i介音,而“真正的”四等韵却是后来才变成这样的。韵镜四等的框架和各类字在四等中的安排跟指掌图完全一样。能否认为韵镜的庄、精组是“假借”而到指掌图才出现介音变化呢?不能。一来守
41、温字母中庄、章组已合流,庄组介音消变在唐末已成事实,二来也无法想象韵镜的作者会知道两百年后的语音状况,预先设计与指掌图相符合的“假借”方案。因此只有相信韵镜四等的语音涵义跟指掌图是一致的。如此,切韵“等韵”的介音与韵图的四等就有如下的对应:切韵-0/ -一等韵一等 -0/ - 韵图四等韵 -r-二等韵二等 -r-三等韵B(庄组)-i-三等韵B(其他)三等 -i-三等韵A(章组日母)-i-三等韵A(其他)四等 -i- 其间变化有两方面:(1) 四等韵产生i介音。如果没有这个变化,韵图一、四等韵就不能同图(现见的韵图四等韵全都跟一等韵同图);如果产生的是别一个介音,那就得有五个等。这就是为什么说三
42、、四等韵合流对韵图体制具有极大重要性的原因。而且四等韵是跟三等韵中的i介音字合流。要是跟i介音字合流,韵图的排列法也会完全不一样。(2) 三等韵B的庄组韵图列在二等,显示i介音脱落,同时三等韵A的章组和日母列到三等,显示其介音从i变为i。这是庄、章组声母合流在介音上的表现。如无此变化,韵图就不可能只给齿音一栏地位,韵图的体制也不会是现在的样子了。 有一个介音变化在韵图里没表现出来,就是轻唇音字中的三等韵介音失落。明白了上述情况,便可知道“假二等”、“假四等”对韵图来说是完全无端的,从切韵的角度说也是不准确的。早期韵图依据中古后期之第二期的介音状况来建立四等的框架,并用这个框架来安排切韵系韵书的
43、字音,其所表示的介音,有的跟切韵吻合,有的就不同。这样,韵图把切韵音系放进韵图四等的框架中,就难免有所扭曲,使之适应中古后期第二期的介音状况。除了三等韵庄组和章组、日母以外,四等韵整类地安排到韵图四等,造成了一种假象,好像韵图四等跟切韵四等韵对应,反而三等韵A类字倒成了“假”的。但早期韵图在另外一方面又尽量迁就切韵系韵书,这就是它的分韵。切韵的许多韵(主要是重韵)在中古后期已无区别,但韵镜等早期韵图仍分韵列图。这是由于韵图之作,本就是为了拼读韵书中的反切,所以要尽可能让韵书中的每一韵、每一小韵都在韵图中占有一席之地。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它成为跟当时实际语音颇有距离的系统。为什么早期韵图有的地方用
44、当时语音,有的地方依切韵呢?从制作者的主观愿望来说,编韵图并非要表现当时的实际语音,而要是把切韵音系图表化,所以依韵书能分则分;但他们不知道切韵时代的介音状况,所以只能按当时的介音状况来安排四等。韵图四等与切韵介音系统的不对应,不是韵图制作者有意造成的。至于晚期韵图如指掌图,则兼顾韵书与实际语音,而以实际语音为主,编篡旨趣跟早期韵图是有所不同的。以上就是笔者对韵图性质的认识。深刻了解韵图,尤其是早期韵图的性质,一方面关系到对中古后期、尤其是第二期语音的研究 陈振寰先生(1986)一方面照韵镜的分韵来构拟五代韵系(pp250-251),是把早期韵图中的仿古成分误认为实际语音;另一方面又认同“假二
45、、四等”之说(p249),这又是把反映实际语音的部分用“韵图体例不善”的老托词再次掩盖起来了。黄笑山先生(1995)认识到四等具有语音意义,但似尚未能真正明了(pp218-220),为中唐五代韵系拟音时也没能完全摆脱韵镜分韵的羁绊(p216)。,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对中古前期切韵音系的研究,值得学界切实注意。参 考 文 献陈振寰 1986 音韵学,湖南人民出版社,长沙储泰松 1988 梵汉对音与中古音研究,载古汉语研究1998:1,长沙 2001 唐代的秦音和吴音,载古汉语研究2001:2,长沙董同龢 1968 汉语音韵学,广文书局,台北金恩柱 1998 唐代墓志铭用韵研究,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46、广州黄淬伯 1941 慧琳一切经音义反切考,历史语言研究所,上海黄笑山 1994 试论唐五代全浊声母的“清化”,载古汉语研究1994:3,长沙 1995 切韵和中唐五代音位系统,文津出版社,台北高本汉 1915-1926 中国音韵学研究(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5年重印,北京赖江基 1991 韵镜是宋人拼读反切的工具书,载暨南学报1991:2,广州李荣 1953 切韵音系,中国科学院,北京李新魁 1980 等韵门法研究,载李新魁语言学论集,中华书局1994,北京 1983 汉语等韵学,中华书局,北京 1991 中古音,商务印书馆,北京陆志韦 1947 古音说略,陆志韦语言学著作集(一),中华
47、书局1985,北京罗常培 1933 唐五代西北方音,历史语言研究所,上海麦 耘 1988 从尤、幽韵的关系论到重纽的总体结构及其他,载语言研究1988: 2,武汉 1992 论重纽及切韵的介音系统,载语言研究1992:2,武汉 1994 关于章组声母翘舌化的动因问题,载古汉语研究1994:1,长沙 1995a 韵图的介音系统及重纽在切韵后的演变,载音韵与方言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广州 1995b 蒙古字韵中的重纽及其他,载同上 1998 “浊音清化”分化的语音条件试释,载语言研究增刊,武汉 1999 隋代押韵材料的数理分析,载语言研究1999:2,武汉潘悟云 1983 中古汉语轻唇化年代考,载
48、温州师院学报1983:2邵荣芬 1981 晋书音义反切的语音系统,载语言研究1981:1,武汉施向东 1983 玄奘译著中的梵汉对音和唐初中原方音,载语言研究1983:1,武汉王 力 1936 南北朝诗人用韵考,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0,北京 1957 汉语史稿(上册),中华书局1980,北京 1982 朱翱反切考,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册,中华书局,北京 1985 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王士元 1979 语言变化的词汇透视(中译本),载语言研究1982:2,武汉谢纪锋 1992 汉书颜氏音切韵母系统的特点,载语言研究1992:2,武汉许宝华 潘悟云 1994 释二等,载音韵学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 北京俞 敏 1984 等韵溯源,载音韵学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北京郑仁甲 1994 论三等韵的介音兼论重纽,载音韵学研究第三辑,中华书局,北京周法高 1948 玄应反切考,载中国语言学论文集,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5, 台北周祖谟 1943 宋代汴洛语音考,载问学集,中华书局1966,北京 1963 切韵的性质和它的音系基础,同上朱晓农 1989 北宋中原韵辙考,语文出版社,北京竺家宁 1992 声韵学(第二版),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台北10
- 温馨提示:
1: 本站所有资源如无特殊说明,都需要本地电脑安装OFFICE2007和PDF阅读器。图纸软件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压缩文件请下载最新的WinRAR软件解压。
2: 本站的文档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图纸等,如果需要附件,请联系上传者。文件的所有权益归上传用户所有。
3.本站RAR压缩包中若带图纸,网页内容里面会有图纸预览,若没有图纸预览就没有图纸。
4. 未经权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将文件中的内容挪作商业或盈利用途。
5. 装配图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保护处理,对用户上传分享的文档内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编辑,并不能对任何下载内容负责。
6. 下载文件中如有侵权或不适当内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立即纠正。
7. 本站不保证下载资源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时也不承担用户因使用这些下载资源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或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