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学的生存论视域
《儒学的生存论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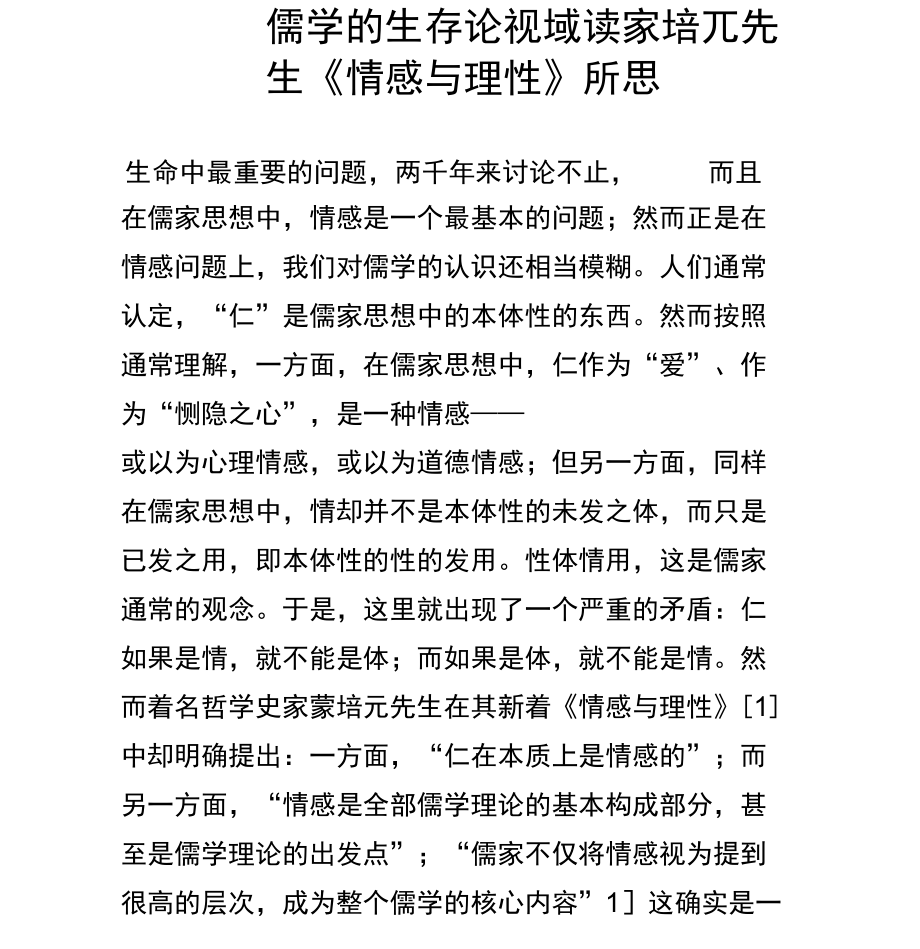


《《儒学的生存论视域》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儒学的生存论视域(23页珍藏版)》请在装配图网上搜索。
1、儒学的生存论视域读家培兀先生情感与理性所思在儒家思想中,情感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然而正是在情感问题上,我们对儒学的认识还相当模糊。人们通常认定,“仁”是儒家思想中的本体性的东西。然而按照通常理解,一方面,在儒家思想中,仁作为“爱”、作为“恻隐之心”,是一种情感或以为心理情感,或以为道德情感;但另一方面,同样在儒家思想中,情却并不是本体性的未发之体,而只是已发之用,即本体性的性的发用。性体情用,这是儒家通常的观念。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严重的矛盾:仁如果是情,就不能是体;而如果是体,就不能是情。然而着名哲学史家蒙培元先生在其新着情感与理性1中却明确提出:一方面,“仁在本质上是情感的”;而另一方面
2、,“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儒家不仅将情感视为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两千年来讨论不止,而且提到很高的层次,成为整个儒学的核心内容”1这确实是一种前所未闻、独树一帜的观点。但是,这个新颖的观点似乎同样面临着如上所说的严峻挑战:在儒家思想中,情仅仅作为体之用,如何可能成为全部儒学的“出发点”、即如何可能充当终极奠基性的东西?所谓出发点,就是这样一种终极奠基性:它为一切存在者奠定基础,一切存在者都被奠基于它。在蒙先生看来,情感更确切地说,仁、亦即爱这种情感就是这样的终极奠基性的东西。显然,蒙先生的新着提出了一个极富挑战性的重大问题:仁爱这种情感在儒学建构中究竟占有
3、怎样的地位?那么,蒙先生是如何处理这个重大的疑难问题的?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行指出的是:在传统的哲学观念下,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这里所谓传统哲学观念,最典型的就是所谓本体论和知识论。这种传统观念是在西学东渐的作用下形成的,它不外乎西方近代以来的三种致思进路一是经验论的进路。格物致知、修身成圣的过程,似乎只是一个经验地实践的过程,而与某种先验的内在根据无关。这种进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符合儒家思想的,但这种符合却是建立在某种误读的基础之上的。譬如人们在谈到荀子的思想时,通常以为他是经验主义的,即是说,人们往往忽视了荀子思想的某种先验论维度。其实,荀子提出“明于天人之分”,主张“制天命而用之
4、”,已然预设了主客二元的对置关系作为前提;更进一步以先验性的“能知”与经验性的“所知”的架构,强化了这种二元对置;最后归结为“天君”对“天官”的宰制,而这就与儒家先验的心学进路达到了某种沟通。这就表明,荀子思想是具有明显的先验知识论色彩的又如有些学者以为,朱子的“格物穷理”也是经验主义的,即是说,他们完全忘记了朱子对思孟心学的自我认同。不仅如此,问题是:其一,对儒学的这种经验论理解势必使儒学面临这样的困境:内在的主体意识如何能达于外在的客观实在?这正是西方经验论哲学所面临的无法解决的“认识论困境”。其二,对儒学的这种经验论理解完全彻底地消解了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途之人可以为禹”的任何可能
5、性的先验内在根据,从而使得儒家修身成圣的诉求落空,成为某种“无根”的妄执。二是先验论的进路。这种进路似乎更切合于儒家思想,尤其是切合于作为儒学正宗的心学的思想人们往往认为,从子思、孟子到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思想是先验论的,因为他们在本体论上预设了先验的纯粹至善的心性本体,在工夫论上强调先立乎其本心,所谓修身成圣,就是返本复性而已。但人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理解同样使得儒家思想陷入一种无法解脱的困境,这同样是一种类似西方哲学的认识论困境的、我称之为“伦理学困境”的处境。这是因为,按彻底的先验论的致思进路,我们必然陷入这样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假如外在的物其实只是内在的心的意义建构,即外在的物实质上原
6、本是先验地内在的,且按儒家心学的设定,心本来是至善的,那么,物的恶如何可能?但另一方面,假如物并不是这种先验地内在的东西,而本来是客观地外在的,那么,内在的心如何可能“穷格”外在的物?我们如何可能穿透心、物之间的鸿沟,而去实在地“格物”?这就是采取西方近代哲学传统的进路所必然面临的困境:内在意识如何可能穿透感知的屏障而抵达于外物?如果不可能,那么,内在的心性修养怎么可能影响至H作用于外在的现实?可见,对儒学的这种先验论的理解最终将使儒学成为一种对于现实问题无关痛痒的玩艺。三则是二元论的进路。西方近代从笛卡儿到康德的哲学,就是这样的二元论进路。笛卡儿的心、物二元论与他的“我思故我在”显然处于一种
7、自相矛盾的境遇;而康德的二元论则又使他两面受敌,亦即同时既面临经验论的困境,也面临先验论的困境。而对于我们来说,对儒学作一种二元论的理解,也使我们同时既面临经验论的困窘,也面临先验论的困窘:假如我们经验地设定外在超越物的存在,我们就面临认识论困境或者伦理学困境;假如我们先验地悬搁外在超越物,我们就堕入对于现实问题的麻木不仁。这三种致思进路的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在划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同时,以作为知识论的根本前设的主客对置这种根本的二元架构作为本体论、可题的底层视域。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过去所理解的中国哲学的“体”与“用”的观念正是这样的传统观念。在这样的观念下,我们所面对的“仁爱情感在儒家思想中究
8、竟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显而易见:假如情感是先验性的本体,我们就会面临上述先验论进路的困难;假如情感是经验性的工夫,我们又会面临上述经验论进路的困难。例如,孟子既然提出“先立乎其大者”、亦即首先确立本心,则显而易见,此“大体”先须被“立”起来。然而,被立起来也就是被奠基,这就是说,心体并不是终极奠基性的。那么我们要问:心体立于什么基础之上?进一步说,如果仁爱就是心体,那么我们要问:仁爱是如何被奠基的?显然,儒学的当代阐释必须另寻出路。我们注意到,蒙先生正是在试图超越那种传统的哲学观念而另辟蹊径。蒙先生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特别地加以留意本书不再从所谓本体论、认识论和知识学的
9、角度研究儒学,而是从存在问题入手,讨论儒学在人的存在、价值及其人生体验问题上的基本主张。1“存在”、尤其是“人的存在”,这些话立即使我们想到一个人,那就是海德格尔。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判定传统“哲学的终结”,转而追问“存在”,也正是从“人”即“此在”的“存在”、亦即“生存”入手的。海德格尔之解构传统本体论,正是奠基于生存论分析的。于是,我们可以想到这样一个问题:蒙先生是否也象海德格尔那样,是采取了一种“此在现象学”的生存论视域?确实,我们可以看出,在蒙先生的儒学解释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解释之间,存在着许多至少在形式上类似的东西:生命存在/存在、人的存在/此在、仁爱的情感/烦的情绪、真情/本真、敬畏
10、/畏、良心/良知如此等等,似乎存在着广泛的对应关系。但是下文的分析将会表明,这些形式上的“对应”实质上却是迥然不同的;而且,蒙先生的整个儒学解释和海德格尔的生存论解释在本质上也是根本不同的。这是因为:儒家的生存论与海德格尔的生存论本就是大异其趣的。海德格尔在前期代表作存在与时间里首先进行了生存论分析,然后进行了良知论分析。良知问题正是儒家思想、也是蒙先生的新着所关注的一个焦点。应当说,海德格尔的良知论分析是相当精彩的;但是在他那里,良知论分析与生存论分析之间却又存在着严重的断裂。为什么这样说?这涉及到海德格尔研究当中的一个重大的疑难问题。众所周知,海德格尔一生的为人行事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
11、与纳粹的关系、他在战后对此的闪烁暧昧,他对自己的恩师胡塞尔、好友雅斯贝尔斯、弟子以及情人汉娜?阿伦特的态度这些都一直在“海学”研究界激起持久的争议。尽管有人为之作出种种辩护,但是无论如何,海德格尔的上述行为存在着严重的道德品质问题;即便不能贸然斥之为“恶”,但至少指之为“不善”,这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于是人们就不得不思考:在海德格尔的所为与其所思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必然的关联?如果我们毕竟承认,善是一种应然的价值选择,那么,海德格尔思想是否存在着某种严重的道德缺陷?对此,有人认为海氏之所为与其所思之间是毫无联系的,另有人则认为应该存在着某种联系,但是迄今为止,双方都未作出令人信服的分析。然而在我
12、看来,儒学的到场将能使这个问题明朗化,因为,下文将会表明,在儒家思想中,良知论乃是由生存论而必然导出的,这就将使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的缺陷、即它与良知论分析之间的断裂暴露出来。这也将表明,蒙先生的儒学解释尽管确实带有生存论分析的色彩,但它毕竟不是海德格尔式的,而是儒家的生存论阐释。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与良知论分析之间的断裂是如何发生的呢?让我们来清理一下海德格尔的运思进路什么是良知?良知是一种呼声:首先,良知是此在对此在自身的召唤。“此在在良知中呼唤自己本身力,这里,“此在既是呼唤者又是被召唤者”。其次,良知把此在从其“所是”“实是”唤起,而转向“能是”“能在”。这是因为,“此在作为被抛的此在
13、被抛入生存。它作为这样一种存在者生存着:这种存在者不得不如它所是的和所能是的那样存在;“呼唤者是此在,是在被抛境况为其能在而畏的此在。被召唤者是同一个此在,是向其最本己的能在被唤起的此在。而由于从沉沦于常人的状态被召唤出来,此在被唤起了”。因此,“呼声出于我而又逾越我”。最后,此在在良知呼唤中从“所是”向“能在”的转化枢纽,乃是“烦”“畏”这样的基本情绪。“良知公开自身为操心的呼声:良知的呼声,即良知本身,在存在论上之所以可能,就在于此在在其存在的根基处是操心”;“呼唤者是在被抛境况为其能在而畏的此在”,“呼声的情绪来自畏”。这些分析确实是很精湛的,但我们的疑虑也由此而起其一,良知的呼声究竟来
14、自何处?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它来自此在这个存在者自身:“在其无家可归的根基处现身的此在就是良知呼声的呼唤者”;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根基上和本质上,良知向来是我的良知”这种解释很好地排除了诸如上帝之类的东西,排除了任何把良知理解为某种“闯入此在的异己力量”的可能;但这种解释也面临着这样的问题:这如何能够避免唯我论呢?如何能够保证良知的普遍性呢?如果良知没有普遍性,又如何能够避免这种情况:任何一个我”都可以宣称他自己的想法就是良知?诚然,海德格尔不仅批评了那种外在超越的解释,而且同时批评了那种“生物学上的”解释亦即个体经验的解释;但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唯我论的解释未必就是生物学的解释。而海德格尔到底
15、并没有正面批判那种可能的非生物学的唯我论。这也不奇怪,在我看来,他的良知论实质上是唯我论的。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呼声来自我向来自身所是的那一存在者”;换句话说,作为单个存在者的“我”就是良知的来源,这个我的所是就是良知的生存论根基。但是,任何一个“我”,作为单个的存在者,仅仅凭他的特殊的此在性,绝对无法保证普遍性的良知。以特殊的此在性作为良知的根基,其结果只能是唯我独尊。其二,于是我们要问:这样一种所谓“良知的呼声”究竟传达着怎样的内容?海德格尔说:呼声不报道任何事件。”换句话说,这种所谓“良知”没有任何道德内容,而仅仅是一种“道德中值”。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它显然是上面的分析所必然导致的结论
16、。然而这样的所谓“良知”,就被描述为了类似王阳明所说的“有善有恶意之动”那样的东西了:单个的存在者对其“能是”这种可能性的倾向,只不过是他意欲摆脱自己的被抛弃境况所是”的冲动这种而已。欲望显然是中性的,即可善可恶的,从而只是一个空洞的形式。但这恰恰不是良知,所以,王阳明才会接着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这就是说,那个“有善有恶意之动并不是良知。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海德格尔所谓“良知”还是有它的内容的,这个内容就是“能在”。良知能够使人摆脱此在的被抛境况,而“能”去“是”另外的什么东西。这种分析当然也算是积极的,但却仍然是纯粹形式的,即是没有任何实质内容的,当然也是没有任何道德内容的。但问题是:良知
17、难道只是一种没有任何伦理价值的实质内容的纯粹形式吗?其三,况且,即便承认海德格尔的良知是有道德内容的,我们还可以问:良知的呼声究竟是必然发出的,或只是偶然发出的?在这个问题上,海德格尔的说法存在着矛盾,这是下文将要涉及的一个问题;这里我们试问:良知的发生若是偶然的,那么此在的生存如何能够保证这种呼唤不是“坏良知而是“好”良知?若是必然的,那么此在的生存毕竟又是如何提供这种保证的?上文已经指出,偶然发生的“良知”是可善可恶的,它因而就不再是良知。但是,此在的生存论分析如何能够保证良知的必然性?这就涉及下面这个问题了前面已经提到,在海德格尔的分析中,从生存论到良知论的转枢是情感,更确切地说,是一种
18、情绪。这种情绪,海德格尔称做Befindlichkeit。这种情绪是奠基于生存的:此在首先作为被抛的所是,而沉沦于烦中,包括对物的烦神、对人的烦心;但是从时间性来看,被抛的所是作为历史性的此在,如果没有对其本真的能在的领悟,“没有时间,就什么也不是。那么,此在如何才能领悟本真能在?这需要另一种情绪,那就是畏。“畏”不是任何具体的“怕”,它不以任何存在者作为对象;对畏来说,“威胁者乃在无何有之乡”;“畏不知其所畏者是什么。但无何有之乡并不意味着无,而是在其中有着一般的场所,有着世界为本质上具有空间性的在之中而展开了的一般状态”,因而“畏之所畏就是世界本身”。这样一来,“畏所为而畏者,就是在世本身
19、。在畏中,周围世界上手的东西,一般世内存在者,都沉陷了。世界已不能呈现任何东西,他人的共同此在也不能。所以,畏剥夺了此在沉沦着从世界以及从公众讲法方面来领会自身的可能性。畏把此在抛回此在所为而畏者处去,即抛回此在的本真的能在世那儿去。畏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这种最本己的在世的存在领会着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这是一番多么地环环相扣的分析!但是我们对此的疑问也是“环环相扣”的:假如“在世”乃是“此在的基本建构”,也就是说,此在总已在世;并且“在世总已沉沦”,亦即“沉沦是此在本身的生存论规定”;而“沉沦之背离倒是起因于畏”,即,有沉沦则必有畏;那么,对于任何一个人或此在
20、来说,这种“莫名其妙”的畏是必然的。但是海德格尔分明告诉我们,畏只是“此在存在的可能性之一”,只是“诸种最广泛最源始的可能性中”的一种,那就是说,畏并不是必然的。假如畏并不是必然的,那么,此在之被抛回自己的本真能在也并不是必然的了,良知的呼唤也就不是必然的To结果我们看到:在此在的所是和能在之间,仍然存在着断裂;而且,这种断裂已必然地蕴涵着生存论分析与良知论分析之间的断裂。这种断裂或许能够提供海德格尔之所为与所思之间关联的某种线索?而这样的断裂,在儒学的致思中、在蒙先生的儒学解释中是并不存在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肯定地说:蒙先生的儒学解释确实具有浓厚的生存论分析意味,虽然它与海德格尔的生存
21、论分析颇为不同;而在儒家,生存论是真正能够为良知论奠基的。今日的儒学研究正在开始透露着这样一种消息:对于儒学的“重建”或者“现代转换”来说,生存论解释学是一种新的极富前景的致思方向。海德格尔告诉我们,西方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维度,以及前面谈到的经验论和先验论的思路,都是源始地奠基于生存论分析的;而我们的问题则是:这种生存论的致思进路是如何在儒家那里体现出来的?在儒学的生存论解释学中,仁爱情感究竟占有着怎样的地位?这显然远不是我们这篇短短的文章所能加以充分揭示的,但我们可以粗略地勾画出它的一个轮廓来。在谈到儒、道两家的基本区别时,人们常说:儒家主张“入世”,道家主张“出世”。儒家之所以主张入世,是
22、因为儒家认为出世是不可能的;出世之不可能,是因为人总是“在世”的;人即便是对他自身的超越,也是在世的超越。于是,我们就面临着对儒家所谓“人生在世”与海德格尔所谓“在世”加以比较分析的课题海德格尔的全部意图在于追问“一般存在的意义”;但在他看来,我们只能“通过对某种存在者即此在特加阐释这样一条途径突入存在概念。因为我们在此在中将能赢获领会存在和可能解释存在的视野”。所谓此在就是人这种特殊的存在者;追问存在的意义只能通过追问此在的存在才是可能的。此在的存在也就是生存,“此在的本质在于它的生存”。这一开始就与儒家的意图有所不同:儒学并不关心所谓一般的“存在的意义”,而只关心“生存的意义”。海德格尔所
23、说的一般存在的“超越”意义,在儒者看来是没有意义的。海德格尔在两种意义上谈到超越:一是存在之为存在的超越意义,一是此在从被抛的所是向本真能在的超越。儒家关心的乃是后者:这样的超越如何可能?人如何能从被抛的所是向本真的能在超越?或者用儒家的话来说:常人从小人变为君子乃至圣人是如何可能的?但儒家确实也是从人的生存论视域切入的。儒家的首要的甚至唯一的关切是人的存在本身、即人的生存。蒙先生书中所说的“存在”即指人的存在、亦即生存,因为在他看来,儒家“将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1。孔子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这种生存关怀的典型表达。但这并不是说儒家毫不关心人之外的存在者,儒家
24、“仁民爱物”“民胞物与”的主张就是关爱及物的表现;但在儒家看来,物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本质上还是人的存在;或者说,物的存在只有在被理解为人的存在时才是有意义的。周敦颐之所以“窗前草不除”就因为其“与自家意思一般”,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儒家不把对人生意义的关切仅仅理解为追问一般存在意义的一种途径而已,因为那样一来,人自己的生存反被工具化了;但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的存在建构的提出仍只是一条道路,目标是解答一般存在问题”。但是,就对人的生存的关注而言,海德格尔与儒家却是一致的。因此,关键的工作就在于对此在即人的存在作生存论分析。这是作为“此在的基本建构”的“在世”决定了的。海德格尔将其视为“首要的存
25、在实情”,而把它作为自己全部的生存论分析的“基础分析”:它领先于全部的本体论、认识论之类形而上学课题,而为它们奠基。儒家也是“将人视为一种特殊的生命存在,并且在心灵超越中实现一种境界”1。而海德格尔也正是经由“生命存在”而达到生存论视野的。他在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中写道:“说到底,当代哲学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作为原始现象的生命上”;正由此,他“要讨论的真正对象被确定为生存”。由于这种在世结构“源始地始终地”就是“向来在先”的“先天结构”,我们必须始终把这个结构“整体保持在眼界之中”。但是,“此在整体性的生存论存在论建构根据于时间性。因此,必定是绽出的时间性本身的一种源始到时方式使对一般
26、存在的绽出的筹划成为可能”。所以,时间性才是生存论分析的根本的源始视域。而说到时间性,儒家的“义”即“时义”或者“时宜”的观念就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课题,此不赘述。就人的生存的时间性来看,海德格尔认为,此在的存在包含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沉沦的方面,即其被抛的“所是”;二是超越的方面,即其本真的“能在”。就超越方面看,海德格尔所提出的最积极的思想之一就是:人“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在于它去存在”;换句话说,“此在是什么,依赖于它怎样去是它自己,依赖于它将是什么。他说:“这一存在者在其存在中对自己的存在有所作为”;“对这种存在者来说,关键全在于怎样去存在”。这样的超越或许才是儒家真正的“内在超越”?因为
27、,在这里,人之自我超越仍然是在世的;这种超越的意义,正如蒙先生所一再强调的,乃是“心灵境界”的自我提升,所达到的是一种超越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的在世观念与儒家的入世观念确实是相通的。海德格尔在对“在之中”的分析中,讨论了“现身情态”:“我们在存在论上用现身情态这个名称所指的东西,在存在者层次上乃是最熟知和最日常的东西:情绪;有情绪。”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一种怎样的情绪?海德格尔特别突出地分析了烦、畏、尤其畏死的情绪,由此导向能在、导向良知。但是正如前文已经指出的,这样的导出存在着很大的问题,存在着某种断裂。而在儒家,儒者的生存领悟不是烦、畏,而是仁、爱。这是儒家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一个根
28、本性分歧。根据儒家思想,并不是那来自“无何有之乡”的“畏”、而是“我欲仁”,导向了本真的能在、本心的确立。所以,对于儒学来说,问题在于:在从被抛的所是向本真能在的超越中,“我欲仁”是如何必然地显现的?海德格尔“直追究到那些同在世一样源始的此在结构上面。这些结构就是:共同存在与共同此在。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样式就奠基在这种存在方式之中”。他解释说:“此在的世界是共同世界。在之中就是与他人共同存在。他人的在世界之内的自在存在就是共同此在。”这种“日常的自己存在的样式”就是“可称为日常生活的主体的东西:常人”。这种常人,儒家称为“小人”,就是沉沦于世的庸人。问题在于,这种“常人”向本真能在超越时的“恻隐
29、之心”是如何被奠基的?或者说,如何“求其放心”?即:“本心”是如何显现出来的?这里,“共同在世与共同此在”起着怎样的作用?前面分析良知问题的时候,我们已然指出,海德格尔的思路并不能保证这一点。但是,本来,即使按照海德格尔的某种说法,仁爱之心也是可能必然地显现出来的。这是因为,“他人的共同此在的展开属于共在”;而“此在作为共在在本质上是为他人之故而存在。这一点必须作为生存论的本质命题来领会”。因为,在共在中的烦或操心分为两种:一种是对于物的Besorge;一种是对于人的Fuersorge。后者可以译为“牵挂”,它又“有两种极端的可能性”:一种是代庖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他人可能变成依附者或被控
30、制者”;另一种可能性是“率先解放”,这是“为他人的能在做出表率;不是要从他人那里揽过操心来,倒恰要把操心真正作为操心给回他。这种操持本质上涉及本真的操心,也就是说,涉及他人的生存,而不是涉及他人所操劳的什么。这种操持有助于他人在他的操心中把自身看透并使他自己为操心而自由”。这种牵挂作为“本真的操心”,就是儒家所说的“戒慎恐惧”;仁爱之心、良知就奠基于这种戒慎恐惧之中。这是因为:从正面讲,这样的牵挂“是由顾视与顾惜来指引的”;从反面讲,这种“顾视与顾惜各自都有一系列残缺和淡漠的样式,直至不管不顾与由淡漠所引导的熟视无睹”。这种正面的顾视和顾惜就是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而那反面的不管不顾和熟视无
31、睹则是儒家所说的“麻木不仁”。行文至此,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了:仁爱情感确实是奠基性的,但并非终极奠基性的。说它是奠基性的,因为在“仁一义一礼一知”这样的建构中,仁无疑是基础的东西;而说它是非终极奠基性的,因为仁爱作为情感又是以在世的生存为基础的。最后应该说,海德格尔的那些分析确实是非常精彩的;但我们同时必须始终保持清醒的是,众所周知,他那些分析完全是没有任何道德内涵的,并不能指向任何伦理学建构。而儒家所关心的却是:生存论分析如何导向伦理学建构?问题的答案或许就隐藏在某种生存论视域中。这可能是蒙先生的新着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奠基是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指对存在建构中的基础或者起源”的揭
32、不。胡塞尔有一个经典定义:“如果一个a本身本质规律性地只能在一个与it相联结的广泛统一之中存在,那么我们就要说:一个a本身需要由一个来奠基。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分析就是一种终极奠基性的揭示。这里仅仅涉及海德格尔的前期思想,以其存在与时间为代表西语“良知”本来并没有任何伦理学的价值色彩,而只是一个中性词,意为关于自身的知识;它虽是对自身的实践活动、包括伦理活动的意识,但这种意识本身是可善可恶的。故有“好良知”“坏良知”之说。参见倪梁康良知:在自知与共知之间,刘东主编中国学术第一辑,商务2000。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56页,汉译者注:“Befindlichkeit来自动词befinden。Befi
33、nden般有情绪感受、存在和认识三个方面的含义。这里,我们将它译为现身情态或现身,力求表明其此情此景的切身感受状态以及这种状态现出自身的含义。”至于道家之所谓“出世”究竟何所谓、出世究竟如何由“避世”“忘世”而可能,则是必须另文讨论的问题。中译本存在与时间译为“操持”。1蒙培元:情感与理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收入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1999年第2版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99年北京第2版。王阳明:传习录下。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邓晓芒译,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1996。论语:朱熹四书章句集注本。海德格尔:评卡尔?雅斯贝尔斯世界观的心理学,路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版。
- 温馨提示:
1: 本站所有资源如无特殊说明,都需要本地电脑安装OFFICE2007和PDF阅读器。图纸软件为CAD,CAXA,PROE,UG,SolidWorks等.压缩文件请下载最新的WinRAR软件解压。
2: 本站的文档不包含任何第三方提供的附件图纸等,如果需要附件,请联系上传者。文件的所有权益归上传用户所有。
3.本站RAR压缩包中若带图纸,网页内容里面会有图纸预览,若没有图纸预览就没有图纸。
4. 未经权益所有人同意不得将文件中的内容挪作商业或盈利用途。
5. 装配图网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仅对用户上传内容的表现方式做保护处理,对用户上传分享的文档内容本身不做任何修改或编辑,并不能对任何下载内容负责。
6. 下载文件中如有侵权或不适当内容,请与我们联系,我们立即纠正。
7. 本站不保证下载资源的准确性、安全性和完整性, 同时也不承担用户因使用这些下载资源对自己和他人造成任何形式的伤害或损失。
